系统地审视历史主义危机
要处理历史主义危机这一问题,有人会先寻找引发历史主义危机的个别病原体,而这些病原体潜藏在哲学、社会学神学、政治和文学创作的新思想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之中。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可取,因为如此一来,史学只作为被动的一方出现,我们也只能从外部观察历史主义危机。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史学在历史主义危机中并不被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主义危机正是产生于史学的内在发展。此外,上述那些尺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既不是与史学相对立的单位,彼此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本身就是更广大的关联系统的表达和影响。而它们自身的变化就是对这一普遍危机的表达。因此,我选取另一条道路,这条路会将我们引向历史书写的内在,也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历史主义危机的产生。我们密切关注的是:历史形象是如何在史学家精神中建立起来的?在危机恶化前,有哪些地方发生了实际的变革或受到了撼动?
而作为对比,历史书写在1900年前后的实践又是怎样的?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1900年历史书写的诸多不同之处;此外,在这一时期,世俗史学家和历史神学家展示出对兰普雷希特立场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后者传播新的历史书写的尝试,反对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的广泛一致。[76]如今,在以兰普雷希特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争论之后到来的一代人非常清楚,当时互相攻击的两方,其立场在许多问题上是一致的,或者其距离并没有当时看上去那么遥远。[77]因此,我们可以将1900年的历史书写视为相对统一的整体。
在历史主义危机恶化前,通行的历史书写有以下四个特征:
(1)关于历史书写对象的特定认识论前提:史学家能够意识到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当对象本身被给出并被确定时,这种主观性只是史学家可以用于观察的一副眼镜;
(2)历史关系或历史关联的学说[译按:作者在后文交替使用“关系”和“关联”];
(3)历史发展或历史进步的学说;
(4)在可能的人类经验领域内对历史陈述的实证主义限制:对形而上学尤其是历史哲学的排除,或至少是对这些尺度的严格限制。
通过联系这四个要点,我们得到了如下四个主题。我们要处理的四个问题是:
(1)处于与从事历史研究的精神的关系中的历史形象,或思想中的历史建构;
(2)处于与其他历史形象关系中的历史形象,或历史联系;
(3)作为在运动中被思考的历史形象,或历史发展;
(4)对处于历史形象“之上”的事物的发问,即“形而上的[发问]”。
历史思考自然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以下在这四个不同要点之下的观察自然也是一种逻辑性的抽象。首先不容误解的是,我并不认为在历史思考的过程中,静态的事物首先形成,随后动态才能得到发展。历史思考的过程借由以下要素得以发生:由史学家位置决定的视界,历史形象和与其他历史形象的关系,以及发展要点,三者在我们精神之中、之间都是不可分离的整体。
在接下来的四个段落中,我要处理的并不是对于四种不同对象的观察,而是对同一对象在四种不同视角下的观察,因此,这一对象的某些要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多个视角中重复出现,事实也不能完全按照逻辑划分。因此,第二部分(历史关联)与第三部分(历史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
1.论思想中的历史构建
当我们思考历史的时候,在我们的思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些有创造力的史学家的思维中又发生了什么?他的读者或听众对他所创造的事物的接受类似一种独特的创造,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仿制——在这里,我们并不考虑这种仿制的情况。
(1)通过梳理将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提及“历史”这个词,我们如果想要有所进展,就必须为“历史”划定明确的界限,因为它的多义性将给之后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比如,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整理出这个词语的许多不同的含义(非逻辑顺序):
a.我最近经历的历史
b.作家X只写历史
c.自然史
d.自然和历史
e.这一惯例属于历史
f.俾斯麦属于历史
g.这一断定有自己的历史
h.法国大革命力图清除历史
i.法老的历史
j.汉斯所著《格奈泽瑙(Gneisenaus)的历史》
k.他在哲学和历史之间摇摆
l.我们思考历史
在这12个短语中,“历史”一词都有不同的含义,或至少出现了细微的差别,这些含义分别是:
a.一种私人的单次性体验
b.一种创作性的讲述
c.对有知识价值的东西的整理编排(希腊词historia最古老的含义仍然存在)
d.在通过人类并在人类身上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上,对于一种重大的、作为总体被思考的实在领域(Wirklichkeitsbereich)的最普遍表达,不考虑纯粹的身体事件(rein körperlichen Geschehen)
e.已经逝去的、消失的和不再通用的
f.对民族而言确有意义且重要的事件
g.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资料,或是前人的经验
h.随着时间流逝产生的状态
i.过去的某一进程
j.对这样一种进程的科学展示
k.历史科学的学习
l.被史学家思考的事件
如果人们想要领会这些被科学、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树立起的对“历史”概念的定义,还可以轻易地找到更多例证。这一事实仿佛指明:区分“历史”的不同含义的方法,要么是引入新的描述,要么是在迄今为止的语言使用中将现存的描述限制在一个更为狭窄、被清晰改写的含义中。因此,人们才提议对Historie[史学]和Geschichte[历史]做出特定的区分。不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并不合适,因为一篇论文的作者不应该苛求读者完全记住词汇。正如“历史”一词的情况一样,紧紧抓住一种表达,以使读者确定地从关联中得出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这种做法是多余的。
通过抛出这个问题,即当我们思考历史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理解的便是“历史”的上述第9种定义,即任何一个历史总体,无论大小——如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或是宗教改革历史,又或者俾斯麦的历史。
(2)那么,历史思考可能并不只是对过去事物的一种简单想象或当下化。
这种对过去事物的简单想象在特定的程度内是可能的。当我聆听一部音乐作品、观赏一幅绘画作品、朗读一首诗歌或阅读一篇哲学论文时,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复习过去人们的“经历段”。当康德书写一个段落时,他带给这个段落的思想一种特定的顺序和特征,而当我以理解的态度阅读这一段落时,我就以某种方式接近了康德的“经历段”,而这部分的康德就是当下的。同样,人们也会说:“我正在听贝多芬。”这在特定的条件(如好的音乐表演和正确的观点)和界限(估计到完全忠于历史的音乐再现的困难)下并不错。但当我“想象”康德或贝多芬,或将他们“当下化”时,或是当我历史性地思考他们时,我的行为绝不是如此。历史思考不是关于特定个体的特定经历段的简单重复。
这一结论十分明确,我也不需要再做出更多澄清。我们在进行历史思考时以某种缩短的方式去体验,以求暂时性地说出这一事物。我们将那些曾经跨越了数年、数十年之久的事件压缩在数小时或数分钟的时间内。然而在我们缩小化的标准中,那些曾经在广阔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在与单一维度准确相符的关系中重现,作为缩略图的事件原本的全部要点在我们这里也并不都是可用的。这样一来,历史思考就会不可拯救地陷入无聊状态,因为有趣的事物在现实总体中本身只占据一小部分,而即使是这一部分也正在消失。历史思考不可能只是一种缩短或缩略性的再现。
但历史思考也不可能是对给定事物的描摹。因为一个被给予我们、面对我们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被我们描述或描摹。在由普遍的、自然导向的认识论所决定的对历史认识问题的论证中,我们会遇到这种观点。这一观点是一种感官感知、一种对实在对象的辨别。但在历史中,我们却与这种在相同意义上给定且可用的尺度或对象无关。我们思考历史时所发生的过程,其发生方式与一种对实在对象的感官感知全然不同。人们常常将历史表达描述为一种历史图像、一幅历史画或类似的事物,但我们不能被这样的表述蒙蔽双眼,因为“历史图像”这一表达本身只是一种形象化表达。当我们将历史思考时在我们脑海中浮现的东西视为“图像”时,它才会成为一幅图像。
但对多数人而言,当他们从事历史工作时,某个具体的图像就是当下的。具体而言,根据不同的身体天赋、视觉天赋、艺术倾向和抽象思考能力,这种图像在不同人的眼中也不同。对他们而言,情况可能是这样:当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路德时,他们就在自己的精神中看到了他,此时是一种克拉纳赫式的图像在产生作用;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在他们的精神中就会出现身着16世纪服饰的教会或世俗达官显贵正在集会的图像,而这种或清晰或模糊的图像是当下的。有意识在读者中唤醒这种具体直观的图像的历史书写者并不少见,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我只需提及勒南(Ernest Renan)和方济各会传记作家萨巴捷(Paul Sabatier)。
很明显,在这种关系中,史学家可能做得太多,并可能混淆史学和小说的清晰边界,正如刚刚提到的两个作家一样。但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一种可能且有根据的处理方式。史学家只支持并引导那些即使没有他们的干预,也能够通过心理学联想在其读者灵魂中产生的东西。而这些绕过了历史思考的具体直观的图像,绝不会超过历史思考所附属的完全次等的要点,它们对原本的历史认识而言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这对于历史科学而言无疑是件幸事,因为如果我们以事实去衡量这些附属性的、绕过历史思考的图像,它们几乎总是不准确的;它们经常只是对图像的模糊记忆,其自身也并不忠于历史(如路德图像),而对那些我们几乎或根本不能从中创造出图像的事物,它们更是无能为力(如公元1000年前后的德意志自然风景)。这种心理联想式的图像与历史思考的内核全然无关,它们在历史思考中虽是对给定事物的描摹,却对此处的论题毫无意义。
我并不需要确保这一阐述不被误解,毕竟我的目标并不是克服“历史图像”这一表达:其一,这种尝试本身毫无成功的希望,其二,反对这一术语的论战与我无关,因为我已经鲜明地强调了对于历史思考而言观察的意义(在其不同的种类和正确的界限内)。
(3)到这里为止,所讨论的一切都很清晰:历史思考既不是一种对于过去的经历序列的简单重现,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描摹。由此,我们得到另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使我们更接近事实真相:史学家从过去发生的事件中做出选择,并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选择的要点进行加工,最终将这些被选出并加工的要点统一为一种历史表达。
这个答案虽然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却可以将我们带上正确的道路。它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史学家历史思考的过程并不像“选择”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在其全部范围内有意识地进行。自然,每一个历史主题已经是从“选择”中产生的,而所谓的资料整理,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史学家有意识的活动:他们以自己对文献(大多也已经是“被挑选”过的)的熟悉程度为根据,在对一场战争前史的描绘中区分主要和次要人物,并为了总体关联分离出重要和不重要的过程等等。但这种挑选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史学家精神中某种看似神秘的功能,因此无需史学家本人的介入。
更普遍的情况是:正如史学家提出“主题”一样,那些进入视域的要点都处于史学家精神中相符的历史分期,并汇聚到一起。而他有意识的工作只是:他以必需的感觉或技巧,批判性地认定或区分在自己的思维中升起的历史思想总体。在他的精神中,对重要与不重要事物的区分,以及历史分组的完整过程,按照观点法则的效果发生。从他的角度出发、在他的环境中、在他自己的一种近乎法定必要性的前提下——即总是以实际的历史技能为前提——这种同样带有强调和“选择”的历史思想形象产生了。
更进一步,许多在史学家精神中汇聚起来的要点,严格来说并不具备“变革”或“加工”的特征。相比那些在“对应面”(Gegenüber)中更早发生过的事件,这些要点是全新的。这些在史学家精神中的要点,包括事实、事实序列和人物,以及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古典、现代等历史总体,在“对应面”中总是拥有某种动力、准则和指令。同时,这些被史学家思索的事物完全符合在“对应面”中已经存在过的事物:前者在充满谬误的构成过程中,必然从“对应面”中得到修正。但这种历史思考本身在“对应面”中并没有事实性的对应。也就是说,通过思考历史,我构成了指涉在“对应面”中存在的某些事物的“想象”和“概念”等等,正是它们意指或代表了那些事物。
历史思想要求具有意义,这一要求曾经以复杂得多、不可能穷尽其描述的方式存在过。史学家不能用一两个词涵盖完整的文化或极其混乱的历史进程,如“罗马与希腊”“1813年的莱比锡”。如果我想要构造“莱比锡战役”这一历史思想,那么这一思想就代表或涵盖了从1913年10月16日至19日在莱比锡的田野和城市内发生的上千起事件。通过思考细节,例如军队调动、拿破仑的行动、布吕歇尔的行动,以及这场战役与之前或之后的政治和战略事件的联系等等,我可以澄清“莱比锡战役”这样一个重大的概念。
但通过思考这些细节,我仅仅构造了在“对应面”中发生的事件的代表。没有人可以把握住事件的巨大数量和如“莱比锡战役”一样的特定历史时空阶段。每一刻在地球上发生的事件,尤其是人类直至现在在可见的历史中已经经历过的事件,都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超越所有人类想象的尺度,而人类只能在这种尺度中寻找并取出某些要点,也只能在代表性的思想中思考这些要点。这个神秘的“对应面”本身并不能被我们理解,它永远处于“对应面”中。[78]
很明显,“对应面”只是一个用于划定界限的概念,对于这里使用的“对应面”概念,还有另一个词语可用,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客观意义上的历史”或“对象”。我并不喜欢使用第一个短语,因为它稍稍削弱了我已经达到的理论强度,就好像“对应面”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构建的尺度,被“主观意义上的历史”再现了。如果人们有意识地排除这一理论,那就不应该反对使用“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这一措辞(至多是因为它的复杂表述)。人们也经常用“对象”这一表达来指涉这个被我描述为“对应面”的事物,而我在上述研究中有意识地避开了这个表达。从逻辑上讲,在“对象”中存在一种包含了“客体”的“对应面”。由此看来,用“对应面”代替“对象”可能也是无意的。“对象”这一表达因其多义性不能采用,因为“对象”不只意味着a.划定界限的概念,即对历史塑造所有可能的激发;它也是b.史学家提出的单一主题,而c.在一些新康德主义者那里,它也是在史学家精神中构建起来的事物。
只有在一个位置上,我们才可以明白、清晰地接触到它:在我们自身有意识的生活界限的内部。形象地说,它在生活总体中是宏大的、永远神秘的事实激流,这激流翻滚着流经“时间”。
近代流行起来的词语“塑造、形象”(Gestaltung)也可以用于表达本文所述的“历史思考”——史学家“塑造”了历史(“主观意义上的历史”)。这一表达被布兰迪(Karl Brandi)使用过,即他在1921年举办的关于“作为形象的历史”的讲座中。我对这一表达抱有疑虑。它切中了与创作形象的思想联系,正如布兰迪强调的一样,历史形象与创作形象有着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但是比这一亲缘关系更强的无疑是这个特定的区别:史学家被“对应面”束缚,艺术家则是独立而自由的。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并清晰表达了这一区别。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在其著作《尼采,一个神话的尝试》(1922,第六版)中没有谈到“形象”,而是谈及“神话”或“传奇” 。他的表达一开始就与本文所论述的“历史思考”产生了共鸣。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史学(指的是历史书写)所创造的图像,相比所呈现的发生在过去的事物,是全新的。但这种全新性在他这里是“一种朝向其他存在类别的转化,是设定价值,而非制造现实”。我们在这里产生了分歧,即分别走向历史书写的道路和英雄赞歌的道路。这本书属于那些来自格奥尔格圈子的“直觉性”历史书写,我将在第二章第四小节回到这一问题。
莱辛在他的《作为赋予无意义以意义的史学》中所持有的观点(首版中没有副标题“或从神话中诞生的史学”)也与这种“直觉性”历史书写相关。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包含夸张、尖锐但正确的观察,但这些观察所呈现的理论言过其实,且未能把握到真正的事实。呈现莱辛的分析需要一篇完整的论文。但除此之外,这本书的主要缺陷在于莱辛误解了一件事:被他称为“意义赋予”的事物并不发源于历史思考的精神,而是根植于“对应面”之中,而在“对应面”中已经存在着无数可用的结构(或者它们已经被置于其中)。更进一步,当我们的表述没有切中问题时,它们无疑是从“对应面”中接受修正。李特在《科学、教育、世界观》中以充分的理由谈到,这种“运用‘神话’的趋势不仅造成误解,甚至导致堕落”——这一趋势最极端的拥护者正是莱辛。
(4)当我们以这种方式为历史思考问题做好了准备,与此相关的一个要点就被阐明了;但只要我们总是期待某种具有单义、稳固结构的对应面,这个重点就不会明晰。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自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历史表达,尤其是重要的总结,总是在过时;为什么政治史、文学史、艺术史、教会史等总是被重新书写;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地达到一种最终确定的表达。我们无法仅用现象的历史观点的变迁来解释这一点。事实上,并不只是观点和对历史事物的判断在发生变化,被展示的历史的内容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阅读19世纪80与90年代的无数杰出历史作品已经不是享受了,尽管我们仍赞同这其中承载的判断,无论这些判断涉及的是小德意志或大德意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神学或反神学、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或自由。
从以上阐述的历史思考理论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个要点。为了把握特定的历史总体,我们偶尔会运用一些在当时有意识的经历中并不存在的概念。比如“反宗教改革”这样的概念,这个在今天被普遍使用的新词出现于兰克(Ranke)的时代;再如“后期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其出现的时期要更晚。我们无法在“对应面”中找到这些词,却在“对应面”中获得了这些概念。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如果我们以认识自然的方式想像历史知识,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现象。
(5)为了理解历史思考的过程,我们还需要接受另外一个要点。为了赢得历史思考,我们必须以某种发问、分类或模式走近“对应面”。历史思考在这一位置上、在其出发点上包含着一个系统性的元素。我们必须拥有某个容器,以从磅礴的生命激流中,从“对应面”中汲取它。例如,如果我想要历史性地展现波拿巴,我就只能依照如下的方式处理:我借助不同的分类建构起波拿巴的历史形象,官员、总司令、政治家、与哲学和教会的关系等等,并将这一历史形象提升至他的历史关联中,在他的历史运动中追踪其形象。只要我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对应面”就会保持沉默。
我同样无需深入地阐明自己以免受误解,因为我并非要借助先定的、抽象的概念为某种建构代言。与我的阐述有关的是在具体直观性中的历史。这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必须或应该踏上由神学教义路线所指引的史学道路,同时闭口不谈所有的倾向史学。
史学家自然不能运用不符合当前时间的分类,他必须持续地监督、纠正这一分类,使其适应素材。
很明显,这种不可避免的系统化切入点带来了许多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个体、民族和文化圈成员的所有经历,都将在我们总体的历史思考中发挥作用。
我们在这一最近得到活跃讨论的哲学(以及神学)人类学标题下提出的所有观点,首先属于大多数史学家没有意识到的历史思考的先定性。舍勒在其敏锐的研究《人类和历史》(1929)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阐述了这些问题,据此,“每一种处于特定人类学中的历史学说都有其根源”(页15):
如今,我们为何看到如此繁多的历史表达,看到社会学家处于残酷斗争中?最深层的原因可以在这一事实中窥得,即在人类的起源、构成和本质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的思想就是所有这些历史表达的原因。(页 14)
因此,舍勒得出,如今在西方文化圈内通行五种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它们各有“其特殊的与之相关联的史学”(页16)。
舍勒区分了:1)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以神为导向的人类学;2)发源于希腊人的“智人”(homo sapien)思想;3)尤其被实证主义所拥护的“劳动人”(home faber)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然主义观点,在历史书写中产生了三重影响[a.作为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b.作为在混血和纯种即种族史中窥得“一切事件的独立变量”的观点;c.作为政治权力导向的历史观点];4)至今在其普遍塑造世界的意义中仍可被理解的狄奥尼索斯观点,此后,劳动人成为了一种“生活的失态”。5)尼采发展出的超人思想,这一思想与哈特曼(N. Hartmann)和凯尔勒(Kerler)所拥护的极端“严肃和负责任的先定无神论”有关,而这一思想在历史书写中的主要代表是格奥尔格圈子,尤其是贡多尔夫。
舍勒的阐述无疑揭示了一切历史书写的一个关键要点。但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都需要得到更精确的研究:这一要点对于一切历史书写是否都是建设性的,以至于我们首先从一种与“人类的起源、构成与本质的思想”相符合的转变中得出关于原子、实用主义和[种族]基因的历史书写次序?舍勒以主观类型学的方式提出的不同思想,在事实性的历史书写中是否在彼此内部得到发展,而使与这五种思想相符合的历史书写形式的支持者难以自证?很遗憾,舍勒并不能更进一步地阐述他关于这一问题域的思想。
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或畏惧总会一起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就触及了深层的无前提问题——或者用曼海姆的概念表示:史学家的立场受限性。这一问题在历史主义危机恶化前很久就已经被论证过,[79]我们在此只作简短表述。
一切不是完全自然的事物都需要被排除,尤其是需要排除认识得以实现的哲学问题。例如,如果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人类认识理解为从外部印象和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状态中得出的产品,那么,这种综合过程实际上在每种认知过程中都在发生,无论认知的对象是自然、历史还是日常生活的过程。因此,我们暂时处理不到这一问题。历史思考的前提问题与这种形式上的先验无关,而与历史思考对象通过我们自身的时空立场所产生的实质影响有关。
我在这里处理的当然不是认识论者的争论。上述阐述的意义仅在于:在这种认识论的形式先验的关联中,即使那些目前通行的认识论并不能被理解,例如新康德学派的认识论,这一情况也与我们无关。另外,在曼海姆《历史主义》那里也出现过此种形式先验、形式和内容之区别的尖锐斗争。曼海姆清晰地指出,这种形式认识论接受了一种在潮流之上伫立、持续存在并通过奇迹与“生成”相联系的主体(页56),并与一种充满活力的、在历史洪流中消解一切的观点相一致。它是启蒙的残余、一种事后补上的建构,符合启蒙时代科学思考的主导类型。
而历史思考对象产生的这种实质影响,所涉及的正是历史思考观点的前后一致性。我既不主张史学纯粹的主观性,也不主张其纯粹的客观性。一切史学都受到立场的限制,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极少能够跳出自身的阴影,因此史学家的立场受限性极少能够被克服。
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主观的”。当兰克在《罗曼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中写下这个被许多人引用的句子时,他不想争论史学家的立场受限性,这一点几乎无须说明。他只是想指出“史书原本是怎样的”,之后他在《英国史》中说:“为了让事物自身言说,我简直希望抹去我自身。”他以史书都是“主观的”这一名言在政治的当下性或未来性影响的趋势中要求历史书写的自由;而希望在自己的史书中抹去自己,则是兰克历史书写中沉思活动的一个或许更加显著的特征。人们不能略去不读“简直”一词,正是它保留了史学家不可避免的立场受限。
但是,如果正确运用了历史方法,在确定的立场上仍会产生一些逻辑上有说服力的、正确的、切中“对应面”并与之相符的观点。因此,即使存在立场受限性,历史也仍是“客观的”:这是一种相对的客观性。这一大胆的表述也已经指出,我们可以做到完全避免这里的“主观”和“客观”表达,也可以只在史学家面对其论题的态度方面,根据他是否保持了论题的公平公正,将这两个表达用作赞扬或责备的词语。
(6)就我们对于问题本身的观察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立场受限的事实,而是我在这里阐述的观点与1900年前后流行的对历史知识的处理之间的差别。当时,人们激烈地强调所有历史知识的“主观”部分,却认为正是这一“主观”部分不可避免地,甚至是极大地模糊了对一种完全给定且具有单义结构的“对应面”的表达。根据这一观点,人们的观察会发生变化,但事物本身总是得到保持并继续存在下去。而根据我们的观点,如此构建起来的事物只存在于人类思考中;但在人类思考中,相同的立场也会产生相同结构的事物;“对应面”并不具有单义且已完成的结构,它不是僵硬的尺度,而是促使历史观点常变常新的无穷刺激。
前文所发展出的被称为视界主义的观点,在我1921年出版的论文《教会史上的古代、中世纪与近代——一篇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文章》中已经存在了(页85),只是Perspektivismus[观点论]这一词语在当时还没有被使用。极具特征性的是,一部分专业史学家强烈抗拒这一思想,除了贝娄(G. v. Below),我曾阐述过他的思想。[80]而这一思想在近代却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哲学层面上得到了根本性的澄清和证实。舍勒在《论人类中的永恒》中明确阐述了这一思想:[81]
历史的事实存在是未完成的,仿佛仍可以被拯救。而一切在凯撒之死中属于自然的事件则一定是完成的、不变的,正如泰勒预言的日食。但是,“历史的事实存在”是人类的意义网络中的影响单位,是未完成的,且直到世界史终结时才会完成的存在。
舍勒在这里的表达与特洛尔奇、斯普朗格、李特、曼海姆、斯特恩(W.Stern)以及哈特曼相关,其中,斯特恩和曼海姆的表述尤为肯定。舍勒和其余研究学者在这里清晰表述的事物,以及我称之为“流动的过去”的事物,在尼采《快乐的科学》的格言 Historia abscondita[隐匿的历史]中已经出现了:
每位伟人都有一种追溯力:他将一切历史重新置于天平之上,过去的千万秘密从它们的藏身之处爬出,暴露在他的太阳之下。我们不可预见,这一切将如何再次成为历史。过去本质上也许总是未被发现而已! 还需要如此多的追溯力![82]
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些表达。无数我们可以认识、思考的结构存在于对应面中,而这些结构又可应用于作为我们思考对象的其他结构,如所有的常规和秩序(生活在其中有意无意地运转),以及个体精神生活所有相对恒定的特征(秉性、智力能力、爱好等等)。这些事物常常具有单义结构,而它们一旦嵌入更重大的历史关联,就会成为问题。即便如此,通过全新的史学处理,历史尺度也很少发生彻底的变化,它自身中存在的所有对立很少会被完全颠倒(为了避免关于特定人物或过程片面且离题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并不考虑非科学力量排除研究出处的情况):
如果我们比较不同时代对于同一文化时期的不同阐释尝试,就可以断定,这绝不是无政府主义。[83]
尼禄(Nero)始终是尼禄,但路德会怎样呢?虽然存在为实现历史“客观性”而做出的努力,天主教与新教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尖锐的分歧,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关联力量”,因为这一历史尺度的“关联财富”。一种历史尺度的关联越贫乏,它就会越靠近历史单义性。从历史角度观察,普鲁士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要比施莱尔马赫容易总结得多。最混乱的是那些身处异常广泛关联中的人物,比如路德——他的作品在1700、1800和1900年前后总是处于全新的重大关联中,以至于历史的“总”观察总是在移动。历史细节和历史“总”体在单义判断的可能性方面非常不同,我们在这里讨论到的困难总是与分化更剧烈的形象和更全面的历史总体有关。正如路德遵循他的性格天赋来生活和判断,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中展开行动,关于这些问题,方法论完善的史学家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应该只是取得同代际史学家的赞同;他们应该使自己的作品跻身更重大的历史关联(即使只是教会史关联),而这将会唤起如此多强调价值的世界观的要点,以至于不同的“总”观点马上就会根据有意和无意的前提条件产生。
我们不能期待这世界上存在一种新教读者可以全盘接受的天主教的路德形象展示。我们可以设想接近对细节及单一总体而非对“总”观点的判断。在这里,整个“新教人”或者整个“天主教人”及其所有构建自身的要点都在发挥作用,这两种根本观点是互相对立的。这种“总”观点与被我们称为“时代”的伟大历史总体共同存在。因此,艺术史的伟大时期绝不是如上所述的那种僵硬的、在“对应面”中总是具有已完成结构的事物,而是随观察者立场的变化而变化。
时代特征总是存在,即使我们随着时代发展顺其自然地以不同方式观看它们,即使我们不能从它们中提取出一种客观适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处于视界法则之下,如同风格(Stile)(许多人希望能从中体认时代)成了视界(观察立场)事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之前观看巴洛克,如今在较远的距离之外看待矫饰主义,而这一转变过程远没有结束。)如今,我们必须以不同于布克哈特时代的方式看待古典艺术(在沃尔夫林所说的意义上),因为观察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Pinder 前揭书,页13-14)
(7)我们的阐述还需要一些界定。我在之前提供的是一种历史思考理论的基本特征,这一表述是我从自己“历史知识理论”的立场中得出的。这个用法包含了一个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已经较为陌生的细微差别:它与1900年的问题相一致,清晰地揭露了为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概念构造上的差别而展开的斗争,并轻易导向一个想象,即史学家所表述的“历史”好像是僵硬地存在于“对应面”中,其结构已经完成,而我们仿佛只需要为了“认识”它而去观看它。
此后,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已经被清晰且充分论证过的历史“理解”理论。这是本世纪20年代人文科学形势的基本特征:人们已经不能再像努力争取历史“理解”一样去争取历史“认识”了。历史“理解”与自然科学认识的分野就令人伤感地变得更加鲜明了,历史“知识”的情形与此相同。在历史理解问题最近被赋予的含义方面,有一点我们必须直面:我们清晰地划定了历史思考理论和历史理解理论之间的界限,并说明了比起那些至今已经以隐含的方式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何没有在自身的关联中更贴近地处理历史理解问题。
不论是与1900年前后的历史知识理论,还是与在这里被阐述的历史思考理论相比,历史理解问题的范围都更加狭窄。然而,“理解”这个词在含义范围方面有一种确定的弹性。我能够找出个别的例子,正如路德在沃尔姆斯对自己立场的坚持,或是像歌德的《浮士德》(Faust)一样的艺术作品,或是——如果可能的话[84]——尝试将大学史理解为总体。这种理解的目标可能是范围非常不同的客体,正如历史“认识”或“历史思考”一样。这种“理解”本身也意味着不同的事物。“理解”可以表示使一个从其关联中得出的尺度变得可理解(路德在沃尔姆斯基于神学发展和自身性格的行为),也可以表示在一个尺度中寻找更深层的内容(如歌德《浮士德》的内容),或者表示寻求切中一种尺度独有的细微差别(巴洛克时代的思想艺术和情感方式),等等。理解理论必须首先研究在我们精神中给定的内容,才能够解决上述任务。一般来说,“理解”是前提,在此之后,历史“认识”或“历史思考”才会出现,并给予“理解”以最终的深化。这种认识或历史思考至少在逻辑上是先于理解的。
因此,现代为争取历史理解所投入的全部努力首先是从施莱尔马赫开始的:这一开端是关于诠释学的努力,也即对于文本和现有事物的正确的、符合事实的诠释问题。然而,如果历史思考在逻辑上更早发生,那么我们针对理解问题的论证所划定的界限就有了根据。而关于“你”“我”之间理解的可能性的哲学问题,以及对如何理解异己灵魂的发问,必须被划定在我们的问题域之外。[85]
(8)我们从上述讨论得出了哪些结果呢?
1)“历史书写遭到了质疑”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这一质疑性的结论并不来自对于被思考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于“涵盖性”概念对历史尺度的构造的讨论。略加思考即可指明,我们所描述的历史思考,与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与他人的交流中发生的事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被史学家实践的思考不是一种独有的思考,它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思考相同——它只是被批判性地美化和规范了。史学家与路德之间这种充满思想性的关系,与他和朋友X或Y之间充满思想性的关系并没有区别;那些和我们一道处于当下交往中的人,同样是我们精神中的思想形象,正如历史过往中的人一样。我们能够在精神层面听到、看到他们;新的精神印象能够加强并纠正指涉“他们”的思想形象——我们拥有把握他们的工具。而在面对过往中的人时,我们同样通过一定的替代品来实现这些操作。所有这些事实在本质上没有改变我们的讨论,因为历史思考就是我们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行事方法,因此,人们无法从中锻造出反对史学的质疑武器。如果人们想要有根据地否决历史科学并断定它并不来自“主观主义”,那么,他们就必须相应地弃绝自己的日常交往。正是由于历史思考被批判性地规范了,它比起伴随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惯常思考才更加可靠和贴切。
2)这种对于历史书写本身的历史思考理论又导致了哪些结果呢?在这里,当然有人要拒绝一切结果,他们会说:
这一理论主要是一种新的历史理论洞见,一种对“对应面”和具有绝对单义结构的给定“客观历史”想象的矫正;然而,1900年的历史书写虽然以某种方式与这一想象相联系,却并不相同。因此,这一历史书写自身可能完全没有或没有受到很强的撼动。通过澄清历史思考在史学家精神中的发生过程,历史思考完全不会被撼动,这一澄清证明,历史思考是一种毫无启发性的错觉。
以下是对这种观点的辩驳。认识论论证并不能直接影响准确的来源加工、纯粹的事实批判和严格保持在准确事实判定的框架中的历史书写,但是对其本质性的斟酌,正如在这里进行的一样,却可以改变或反作用于历史书写。哲学家将认识论研究当作自己的私人事务,于是一切都保持原样——这种观点确实在之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事实上,当这种思想在他们的领域中出现时,事物一定以某种方式或在某个位置上改变了自身。新的历史理论洞见一定会反作用于事物本身。
这一结论至少在确定的界限内是事实。回忆我们到此为止得出的主要结果:在僵硬、具有单义结构的“对应面”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种流动的尺度,它总是追求新的历史形态。首先,这里涉及的是我在本章上一节阐明的事实,即历史书写和哲学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但这也绝不表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必须成为“哲学”的某一部分。史学家的个体天赋和历史论题的提出将以无数的方式产生,其中包括了那些显示出小部分哲学特征的方式。在1900年前后,人们认为在史学和系统性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本质性的二元对立;而将历史书写视为哲学的专有性只能排除上述二元对立。斯特恩伯格(Kurt Sternberg)以充分的理由谈到“历史性与系统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这种广泛传播的观点的错误性,即历史性可能缺少系统性,或与系统性彻底对立”。
第二,从对一种单义结构的“对应面”的否认,以及对这种对应面显著分化程度的深层洞见中,我们得到了一种提升史学家的责任。贝克尔强调:“塑造历史的去客观化导致史学家责任的巨大提升。”李特也在其著作《科学、教育、世界观》中也说:
在每一种思考同时也是决定之处,每一步都必须被考虑,每一种判决都必须被权衡!
第三,一种纯粹冥想式的历史态度的可能性遭到了质疑。事实上,特洛尔奇要求的文化综合性历史,与兰克冥想式的历史书写间存在巨大分歧。但这一分歧马上得到了消解,因为实际上既不曾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面对历史材料纯粹冥想式的态度,同样,也不曾存在过一种绝对不具有文化综合性质的历史书写。冥想式历史书写的专心致志的倾向,与通过观察历史瞥见未来形态的愿望总是并存的,史学家自身的倾向、性情以及时代状况可能会导致历史书写在不同时代更多地偏向其中一侧:激昂的时代偏爱文化综合,而沉静的时代则偏爱冥想。如此,人们就也可以在20年代历史主义危机的疲乏中听到对冥想历史书写的呼唤。
不妨引用威斯特法尔对马祖尔(G.Masur)《兰克的世界史概念》的富有特征的评论:
因此,我们越过当下德国精神史的倾向,重新将目光落在被忘却、被否认了可能性的目标上:一种“在纯粹沉思中把握了事件总体的世界史”。[86]
而我既不会进行纯粹的沉思,也没有掌握事件的总体。
2.历史关联
到此处为止,我们已经在暂时不考虑历史关联的情况下讨论了历史形象和历史发展。现在,我们将在观察中继续前进,研究处于与其他历史形象的关系(联系)中的历史形象,即被我描述为真正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us)的事实。首先,我假设那些几乎总是与“相对、相对化、相对主义”(relativ, Relativität, Relativismus)有关的劣等次要意义可以被避开。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词组的语言使用进行检验,以肃清我们表达的障碍。
如果人们认为“相对、相对化、相对主义”等词汇来源于“联系”(关系),那么“相对”就只能表示“处于与……的联系中”。但这一原始而有意义的含义在语言使用中却被遮蔽了。人们使用这样的表达——“这相对正确”“那个相对较大”,此时,这个词表示“近似”“不完全”“相当”;其原始的含义虽然存在于背景中,却不再被清晰地思考。如果有人说,“他非常相对化地描述了他的对象”,这是说他将真正重要的事物悬置了。在这里,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进一步退回到背景中。除了原始含义的这种广泛的变形,“相对、相对化、相对主义”这一词组在历史理论问题领域中的使用则是如此:人们要么在史学家表述的适用性和适用范围方面,要么在历史尺度的性质方面运用这一表达。在前一种情况下,历史评判是相对的,在史学家和历史尺度之间存在联系;在后一种情况下,历史尺度是相对的,在该历史尺度和其他历史尺度间存在联系。
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的问题与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史学家的立场受限性没有区别。这里,“相对”这一词汇与“主观”含义相同。“相对”这一词语群组的用法在语言和事实方面都没有异议。这里的思想是:历史评判与评判者有关。这一用法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尽管如此,我仍要从”相对“这一词组中分离出这一含义,不只是因为立场受限性的问题在上文已经讨论过,更是因为“相对主义”这一描述在史学家立场受限之下的运用导致了这样的假象:历史思考在立场受限性方面成了一种重要的特殊情况,这一特殊情况将史学降为次一等级的学科。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此外,如何在史学家和“对应面”的方面运用“相对、相对化、相对主义”这些词,也很棘手。语言使用在这里如此摇摆不定,以至于同一个词有时甚至会表示完全对立的含义。“相对”一方面意味着史学家的判决被“主观”浸染且总是受到立场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尝试克制自我判决,尽可能突破立场限制,从历史尺度本身的关联中向外理解尺度,并理解其对于当时时代的合理性。许多人进一步将“相对主义”理解为历史质疑,即根本性地或在特定情况下强调历史知识的不稳定性,例如历史上耶稣的可认知性问题。这种态度声称,一切历史陈述都是完全可疑的。这种语言使用是如此拙劣,以至于我们无需再继续探究下去——在这里,“相对”等词语已经与其原始、直观、真正的含义相距甚远。
接下来,我们不再在史学家的立场受限性方面运用“相对”这一词组,而只将其用于历史尺度及其他历史尺度之间的关系上。“新柏拉图主义是相对的”这句话,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尺度与其他的历史尺度有关”,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我们就遭遇了这一词组对于史学的决定性含义。这里,“相对主义”与历史联系、历史关系或历史关联理论并没有不同之处。这种“真正”的相对主义从18世纪开始逐渐形成,在1900年左右的“历史主义”中得到完善发展;与此同时,之前的历史书写则在原子论中不断发展,并在特定的切入点或初级阶段中认识了历史关联。
历史关联处于(不论是否已经被过去的人认识)普遍的双重类别中,它描述的要么是实质意义上的历史影响(如普罗提诺的思想受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要么是历史尺度的存在、影响、本质在其得到实现的意义上的前提(如基督教作为一种普遍的、超国家的宗教,是通过罗马帝国内地中海国家的政治关联得以实现的)。
对于这种历史思考而言,建立关联必不可少。假设我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某处土地上发现了一块带有题词的大理石板碎片,一旦我开始建立关联网络并寻找到这一网络的某些线索,这块碎石对我而言首先就是历史的。正如历史事实一样,可能的历史关联的数量是不可预料的。随着物理时代的过去,早已逝去的历史尺度又增加了新的关联。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胜利使通用希腊语成为可能,但通过希腊语新约的每一次再版,历史也建立了遥远但全新的关联。最后,俯瞰历史中所有尺度关联的理想将成为可能。那些已经逝去、我们根本不觉得重要的尺度,在未来时代的状况下仍可能发挥重要的影响。这样看来,过去并不是僵硬的,而是有活力的,是持续变化和生长的。
我们若以这种方式全面一致地思考历史相对主义,便会浑身战栗。历史相对主义是一种极其巨大而不可全观的网络,它带有数百万的网孔,网线以一种互相缠绕、几乎无法理清的方式编织在一起,并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一种历史尺度获得了生命,这有赖于其他特定历史尺度之间可能仅有一次的相遇;而相遇的尺度又会一起显示出仅会出现一次的资质;因为每个单一的、决定其他尺度的尺度,其本身又被数百、数千个其他尺度所决定,深深编织在历史关联中,这一关联将它和它的环境、它同时代的其他尺度联系起来。这种历史尺度本身与一种关系总体并无差别,它是某种受一个或多个特定承载者作用的集合(但不是僵硬的,而是一个总在流淌、移动的集合)。
例如,“基督教”的历史尺度是通过在特定关系中彼此相连的特定思想、感情和快感构建起来的集合。但同时,现存的关系总是经历着不同的分组和重读。一种历史尺度一旦形成,就会马上开始变化:不只是构成尺度的元素在波动,该尺度与其他尺度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被其他关系替代。每一个尺度都有一种或强或弱的关联力量,一种建立并保持联系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增强、减弱、最终被耗尽,于是这一尺度就不可避免地被过去的幽暗深渊所吞噬。在无数国家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波动、形成、变化和消逝的过程。
从这一简短的解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1)历史相对主义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
(2)人们在历史事物的领域内必须避开“相对”这一概念充满缺陷、劣等和糟糕的次要意义;
更切近的观察表明,对历史“相对主义”态度的普遍指责实际上是混乱且毫无根据的。绝大多数的指责指涉我在上文已经分离出去的“相对、相对主义”词组的含义。想要战胜“历史主义”,就必须看到与此相联系或相一致的相对主义。我们将证明,这些对相对主义的指责并不涉及真正的相对主义。
这些指责认为,相对主义削弱了行动力量,招致了怀疑和自满的情绪;否认精神的独创性;根除了所有的规则和价值:不只是国家和法律生活中的规则与价值,还有宗教、道德、艺术以及思考形式,即逻辑中的规则与价值。一种尺度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产生并根除以上的规则和价值,这一过程已经得到了证明。同时,由于这些关联是一次性的,它们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瓦解并永不复返。
这些针对相对主义的思考和疑虑在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异常活跃且反复出现。同时,它们也给那些由于特定原因视严格的史学为可怖或毫无体系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这些疑虑并非不可克服。
(1)行动力量的缺乏、怀疑和自满并不一定伴随相对主义出现,由于其他原因,它们实际上已经存在,只是与相对主义关联了起来。相对主义去除了遮蔽,使事实状态赤裸地显露出来。但这种去除对个体的影响却极大地取决于个体本身。一个人朴素且不抱有任何美化目的地考虑了所有情况后,表明他的体质非常虚弱,并预计自己不会长寿,那么,这种情况会使他压抑,强迫他进入无所作为的状态。但是,这种无所作为并不只由这种思考本身引起,同样也与这个个体的性格有关。
在其他的禀性条件下,上述考虑完全可能带来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影响:它可能会激励富有生命力的活动。历史相对主义也并不一定导致无所作为和自满情绪。如果那些被巨大欧洲危机所激发的行动主义者们认为,历史相对主义应该对这种无所作为和自满负责任,那么,他们就忽视了上述事实:相对主义完全可能导致相反事物的出现。它可能赋予行动主义以灵感,因为它阻碍了奴隶化成为历史中的生活形式,并给予人类从历史重担下解放出来的自由感觉。它不一定削弱,反而可以提高和充实生命。通过指出我们自身所处的重大历史关联,相对主义可以给予我们的存在以意义和形式,并去除所有偶然和无意义的特征。
(2)同样,导致对精神独创性的否定的,并不是相对主义本身,而只是对它的错误运用,这种错误混淆了条件和原因。一个像歌德那样的天才完全是相对的,他受到多种多样条件的制约并依赖于它们,因此并不能通过推论得到。对独创性的奇思式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比如幻想一种哲学思想可能的创新范围和它相对于之前哲学的独立性——将通过历史相对主义得到本质纠正。
(3)最后,相似的情况发生在规则和价值的问题上。自然,规则和价值也处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之中;因此,它们也都是“有条件的”。例如,古典时期希腊的审美理想与哥特或中国的审美理想有根本性的不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无可争辩的。历史相对主义使我们从不同的历史关联中理解这些差异,作为史学家的史学家能做的只是揭示出所有的差异,并使人们能从历史关联中理解单个历史尺度。如果他接受了这里面的任何一种价值,比如古希腊的审美理想,并将其视为绝对价值,认为它普遍适用且是判断所有其他事物的标准,那他就逾越了作为史学家的能力界限,也剥夺了自己对其他事物的实际理解。需要补充的是,史学家不能为了自身而拥有审美理想:他必须像没有审美理想一样去考察和接受审美理想。他必须每时每刻排除自身的理想,从而能够将自己置于每种不同的立场中。
真正的史学家必须在这种对相对主义的使用中发展出一种精湛的技艺。他必须能够适应这种巨大的财富和无数的现象,这就是说,要前后一致地、相对地思考。这是一种观察实际历史的方式,它以不可穷尽的事物为目标,并与尽可能多的事物进行比较;与此相对的则是一种史学上的自足态度,它遵循就近原则,认为自身对于事物、规则和价值的判断就是绝对的。难道史学家应该放弃前一种而采纳后一种吗?那将引致史学的贫乏化和愚钝化。
也许一些人只是从“历史主义哲学家”狄尔泰那里了解到了这种价值之无政府主义的名言。狄尔泰在他70岁生日的一次演说中将“价值的无政府主义”描述为“自格林、柏克(Boeckh)和兰克以来伟大历史科学的结果”。这是时代秘密的本质感觉。在如今仍然可见的狄尔泰关于此次演说的手稿中,还存在另一种表述:
每一种世界观都在历史层面上被决定、被限制,因而是相对的;一种可怕的思想无政府主义似乎要从中诞生。但是……世界观被建立在最终的表达性精神与自身的关系和宇宙自然中。因此,在我们的思考界限中,每一种世界观都表达了宇宙的一个面相;每一种都是真实而片面的。我们没有机会总体性地观察这些面相。我们只能在不同的被折射的光线中看到真相纯粹的光亮。[87]
这句话使人感到惊恐,但这种价值的无政府主义确是事实;而沃格尔·施特劳斯(Vogel Strauss)的策略并不能帮助我们战胜这一事实。历史相对主义证实而非导致了这种价值的无政府主义。史学家尝试确定并理解这一事实;而对于那些宗教、道德和审美性的人而言,这种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是实现人们所认知的“最高价值”并使其在与其他价值的斗争得到承认的一种推动力。这种对规则和价值权利的剥夺,在纯粹历史论证领域、在对规则和价值存在根据的说明中很少发生。如果对事物的历史观察能够根除规则和价值,那么这句话反过来也仍然成立:史学能够树立起规则的适用性。实际的规则和价值塑造独立于理论判定;后者只能产生补偿性作用。因此,应用于规则和价值的历史相对主义是无害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这种意义上,相对主义绝不会被历史主义危机克服,至少绝不会被这些氛围和疑虑征服。但它会被其他的权威克服吗?表面上看,在一些重要的“直觉性”的历史书写中(我们还会提到这些历史书写),历史相对主义好像确实被克服了。当我们阅读贡多尔夫对于观察历史现象深层内容的相对性之难点的阐述时,我们很少会意识到历史相对性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难道因此就不存在了吗?
贡多尔夫自己一定不会争辩相对性世界的存在和研究该世界的必要性。但在具体的表述中,他认为史学的任务并没有被穷尽,与此相反,史学任务更重要的方面是对历史尺度深层内容的展示。在最近其他的“直觉性”作品中,比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相对主义甚至被拔高到此前颇为少见的程度,因为在这里,数学思考甚至被证明与孕育了它的文化具有相对的关系。
正如平德首先发展出的结论一样,相对主义也被现代的代际学说抬高了。代际学说得出的不仅是单个时代,也是单个时间节点之间的分化特征。平德敏锐地指出,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已经或多或少预期到的简单的当下根本不存在,因为处于完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经历了每一个历史时刻,而它对每个人而言的意义都不相同。不同的时代更是如此。相同的时代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同的时代,是他自己的、只与同龄人分享的一个不同的时代。[88]
最终,雷斯岗(Hans Leisegang)极大强化了对“思考形式”相对性的洞见。[89]
上述意义上的历史相对主义当然不能被克服。当历史关联的塑造对于历史思考而言不可避免时,具有绝对性的、从联系网络中提取出来的单个历史尺度,也就当然不可能存在。这种意义上,绝对便是非历史,历史则是非绝对。“历史性地思考一个尺度”指的是在其历史关联中思考这一尺度。这自然也适用于在历史中出现的宗教尺度。不容否认,对上帝信仰的想象内容完全处于特定的、变动不居的关系中。基督教对神、对天父的想象就与带有族长统治烙印的家庭集体形式有关。而对于发展贯穿了两个代际的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言,伴随着家庭的完全消失,在基督教意义上将神作为父思考的可能性也将彻底不存在。对这些人而言,基督教的预言不可能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至少是基督教的上帝思想中与“父亲”形象有关的联系——建立起任何联结。伦理价值的情况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代表人与人之间最基本关系的价值,如爱、忠贞、真诚等等。这些伦理价值在某些时候首次出现或被“发现”;而发现了它们,只要我们不堕回野蛮状态,就无法超越也不会失去它们。同时,这些价值也必须在丰富而数量巨大的人类事物中不断得到新的实践,并争取自己的适用性。它们处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这些历史关联不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自身;这些价值从各自的历史情境中接受了自身的色彩,即自身的感觉差别、语言表达等等,它们在对自身不利的关联中可能被遏制,在自身的存在中也会遭受威胁。
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历史主义危机,历史相对主义会不受影响和改变地继续存在下去。同时,我们可以在海姆(Karl Heim)的著作《信仰与思想》(Glaube und Denken,1931)中发现,相对主义思想在神学教义领域中得到了一致而彻底的实践(页279-295)。此外,曼海姆的研究《历史主义》也涉及对相对主义问题的根本的历史哲学论证:
不存在一种对于所有时代、所有要求都适用的概念;绝对性自身在每一个时代都以不同的方式构造自身。(页58)
3.历史发展
即使历史形象在史学家精神中被构建,并被置于与其他历史尺度的联系中,我们也仍未获得这一形象:我们必须同时在时代的方向和运动中思考并理解它。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深层的发展问题。
我并不需要描绘[90]“发展”这一概念如何在18世纪出现,其对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又有哪些全面的含义——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发展”概念互相影响并得到了提升。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19世纪的历史书写中,“发展”是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完全给定的尺度,人们认为它足够透彻和清晰,理解它并不需要一种更加鲜明的本质性表达。
而这一情况早已改变。如今,发展概念遭到限制甚至质疑。我们尝试总结这些批判性的抗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作出澄清。
(1)我们从一些关于进步思想的评论入手。进步思想被许多人蔑视——作为欧洲一场巨大灾难的结果,这种态度可以理解。欧洲文明将自身提升为最为精密的技巧,并导致了自我毁灭的巨大灾难。人们从世界大战阴沉而散发着滚滚黑烟的废墟处回望,看到19世纪处于一种全然不同的光线中,就好像它完全在自身中独立存在并产生影响:19世纪仿佛完全将自己献给了宏大而堕落的“进步”错觉。这种独特崇高的文化感充满了战前时间,现在却被忧郁的文化批判所替代,后者尤其出现在史学领域。如果这种文化批判不受限制并崇尚进化论、信仰进步,这该多好!
事实上,19世纪并不像现代文化批判所相信的一样,完全处于“进步妄想”(Fortschrittswahn)的范围内,但这一妄想凭借其普及但模糊的形式已经传播得足够广泛。自由市民阶级首先拥护这种进步思想;随后,社会民主的工人群体最终进入了历史书写——至少是进入了较低层次的历史书写。总体而言,这一“进步”思想仍含糊不清:究竟是什么在向前发展?是作为整体的文化吗?但“文化”又是什么?这种文化发展的动因是什么?这背后的原因或者神秘力量是什么?人们如何能够“实证”地否认所有形而上性,同时又相信这种“整体”的“进步” 、“文化”的“进步”?这难道不是纯粹魔幻的妄想吗?在这种模糊而夸张的形式中,进步信仰作为对整体、文化等要素之进步的信仰,实际上毫无价值,本时代的文化批判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首先,对这种激进进步思想的谨慎批判在历史主义危机出现之前已经活跃很久了。特洛尔奇在海德堡大学1911—1912冬季学期的课堂上展开的关于“信仰学说”的一些讨论,可以作为例证(出版于1925年,见页320以下):
我们新近获得的历史知识,即地中海民族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关联性的、最终导向基督教的统一体,支持了这种关于持续的、汇集一切的进步的设想。以此为基础,我们应该能够设想欧洲文化和基督教的发展,并得到对于伦理宗教生活的组织材料之基础的大胆想法。然而,由基督教统治的欧洲文化总体只是总历史内部的一小部分;关涉宗教和文化最终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对于一种统一并提高一切的进步的信仰,不仅能够攻克并夺取伟大文化圈的疲乏和耗竭状态,也有悖于那些从新情况中产生的全新的斗争和困难。而将人类的终极状态视为一种统一的尘世完满,则同样困难,因为生活态度的巨大困难更加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普遍的提升性进步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期待一场在新战线上出现的新斗争。
其次,没有人能够证明,这种进步妄想决定了1900年前后的科学史学。1900年前后的史学家所谈论的进化论,与真正的进步信仰全然不同。当时,一位主要的史学家梅耶(Eduard Meyer)曾谈到这种“妄想信仰”:“地中海民族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91]在自兰克以来的德国权威史学家中,真的只有这一位受到了“妄想信仰”的影响吗?[92]兰克自己始终怀着对于“日常精神进步不间断的持续”的信仰,以及对于“物质和精神进步”的信仰,但这绝非没有限制。
(2)在历史主义危机恶化前,史学的代表人物就已经并无克制地谈到了“发展”(Entwicklung);在更早的18世纪,“发展”概念就已经在史学中存在,它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在历史事物中观察到的变化:
若要从历史中得到教诲并变得睿智,单个历史时期便是最精彩的戏剧——人们可以从中注意到人类精神的发展。 [93]
黑格尔哲学使“发展”概念被进一步接受,[94]同时,这个词独立于黑格尔思想的用法并没有废弃。正因如此,它的使用并没有因黑格尔哲学的衰落而受到遏制。在这一方面,立敕尔对《古天主教会的产生》这一作品的两个版本(1850,1857)的比较十分有趣。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立敕尔与图宾根教会史学家鲍威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在历史书写方面的决裂,后者受到了黑格尔的极大影响。这一决裂主要表现在:立敕尔有意识且充满活力地背离了鲍威尔对天主教会发展的建构,这一建构从犹太基督教和保罗基督教两种元基督派别中产生。也就是说,立敕尔抛弃了黑格尔—鲍威尔的三步历史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但他在第二版中却像以前一样公正地使用了“发展”概念:他反对尼安德(Neander),并指责后者“仅将事件视为对可证明的发展的解释甚至替代”(页7)。[95]
“发展”概念仍被使用,甚至被正在涌现的自然科学高潮提升到新的高度。然而,史学家却常常拒绝使历史的发展概念靠近或适应生物学的发展概念。[96]在1900年前后,人们相当自由地使用“发展”这个词语,例如,人们经常在历史“整体”或者“历史运动”的广阔意义上使用它;或者不加批判地使用它,将其视为一种不再通用或不再被接受的形而上学难以理解的残余。也即是说,人们将“发展”想象为一种穿越时代并向前推进的实体化本质,而没有觉察到这里呈现出的是一种加密的形而上学。
弗莱施曼(A. Fleischmann)和格吕兹马赫(R.Grützmacher)于1922年以“当下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发展思想”为标题讲授的课程,提供了从动物学和神学对于发展思想的批判。格吕兹马赫指出,对于普遍历史、欧洲文化史(尤其是哲学史和艺术史),以及习俗生活的历史及其理念,最终还有普遍宗教史和基督教历史,“发展”思想过于狭隘。正如不同的生命领域显示出历史运动的不同类型,它们也经常处于不可预测的波动中,绝不可能保持普遍的持续和上升状态。根据格吕兹马赫的最终结论,“发展”思想的源头不是严格科学性的思考,而是现代的劣等神话,它以幻想的方式重新解释并微弱地补充了现实的事实构成。
这样看来,人们部分通过哲学思考,部分通过史学的自我修正取得了两个进展。
第一,就“发展”最严格的意义而言,如今人们只有在自然天性的特定过程中才能谈论发展,严格地讲,即只有在本体论的确定过程中谈论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对个体存在的特定生命过程进行科学改写。毛毛虫发展成为蝴蝶。这是实际的、真正的发展。在这里,我们首先能够证明一种以特定且合乎规律的方式通过不同形式发展出来的躯体物质。同时,这已经处于种族发育,即处于整个生物群体的变化学说中了。如果种族发育“指的是脊椎动物大脑的发展”(我在这里引用杜里舒[ Driesch]的说法,下文同),那么,
形象地说,发展的不是脑形式的序列,而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事物,“大脑”只是组成了其中的一个表达面相。[97]
第二,在史学中,人们必须要阐明这个表述的意义:“一个国家或教会在发展!” “教会和国家”这类词语实际上掩盖了异常混乱的事实;而当我在运动中思考这些概念时,情况甚至更加混乱。根本而言,并不是事实在运动:事实总是不同的。更确切地说,随着新的条件和局限不断出现,总会有新的事实被确立。当我在一种时间序列中思考这些事实时,这一序列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发展。事实上,这完全不是一种自在自足的发展,而是一种被我构建起来的关联,我从被称为“对应面”的宏大、不断向前涌动的生命激流的特定要点中将它塑造出来。作为一切被思考的历史对象的基础,这一“对应面”不断向前运动。人类心脏从生到死的跳动就是这种运动的起点之一,同时也是这一生命激流最为可感的起点。
由此可见,史学家描摹的单个发展是一种由他所思考并构想出来的发展。当他建立了abcd的顺序,这些尺度在“对应面”中就拥有了自己的对应物。这些尺度并不以孤立或与彼此直接联结的形式出现,而是带有与无数其他因素的关联。因此,诸如被史学家思考过的尺度b直接由a“发展”而来,而c直接由b“发展”而来等等之类的说法,都是欺骗性的表象。这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发展。
史学家总是能够在某种界定中塑造出这样一种历史的“发展”关联,而向前发展的生命激流绝不能作为整体进入一种历史关系总体。首先,只有这种生命激流——“客观意义上的历史”——最终到达终点,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历史思考的精神战胜这种生命激流。其次,人类不可能“理解”这一生命激流,因为它作为整体是无法类比的一次性进程,正是由于无法类比,人类便不能理解它。最后,只要这一生命激流仍在涌动,只要我们还能够俯瞰其全貌,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绝对没有任何连续的要点能够成为一种历史关系总体的中心或“主题”——我在自己的校长就职演说中多次提及这些思想。[98]
同样,也不存在一种能够横跨所有时代和民族,且被一种连贯思想统领的普遍历史。除了我在《教会史上的古代、中世纪与近代》中的论述,特洛尔奇也同样强调了这种普遍历史的不可能性:[99]
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会作为统一的历史对象而存在。因而,把握或践行一种作为整体的人类发展史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整体的人类没有精神的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统一的发展。人们对此已经阐明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形而上学童话讲述的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主体。
海姆的出发点与特洛尔奇不同,但同样严厉地拒绝了这种普遍历史:
世界史的每一幅图景都是一种建构,这些图景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中寻求悬置冲突。它只是一种对视界的接收或从一种特定立场出发、由主体“我”的观点勾勒出的图像,在其中我们又通过投射接受他人的立场……真实历史是历史图像的战场。它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对立的历史建构互相争斗;世界史的诸多幻象被从不同的立场观看,同时也被互相质疑,每一种幻象都徒劳地尝试在自身的体系内排列出对立观看的次序。[100]
此外,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中,尼采也否认了普遍历史。[101]
与对普遍历史的批判相适应,也不存在一种通用的世界历史分期。我在自己1921年的书稿中尝试深化这一问题,而贝娄(G. v. Below)在其讲座《关于历史分期》(Ü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102]中向我发起的论战,一部分纯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一部分则在于贝娄没有看到根本问题。[103]鉴于我已经做出了我认为必要的论述,我将不再处理这一问题。贝娄与我观点的主要区别在第611页的第二部分显示得尤其清晰:于我而言,将“中世纪”和“近代”想象为统一尺度是对“世界之年”(尺度A)的古老想象的美化和后续作用;而对于贝娄而言,这则是一种“关系总体”(根据我引入的描述,是尺度B)。
贝娄并未与我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因为我所理解的尺度A(即使以被修饰的形式展示)与一种“关系总体”有着不同的构建方式。关系总体首先要求一个表述清晰的特定主题;它的构建并不是仅仅通过事物、表达形式、宗教想象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普遍而持续的存在,而它们在所描绘的历史形象中是背景还是前景则并不重要。贝娄在他的回复中完全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他认为我之所以排除了“中世纪”和“近代”的概念,是因为我在事物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普遍联系,他这是完全说反了。对我而言,正是因为太多的关系总体同时存在并相互交叉,所以才不可避免地必须打破由之前在历史洞见方面远落后于我们的时代所创造的原始而人工的“中世纪”和“近代”框架。
约阿希森(P.Joachimsen)给出了我与贝娄展开的讨论的概要,[104]他在所有关键点上都赞同我的看法;而如施奈德(Fedor Schneider)之“贝娄向我证明了普遍时期的存在”[105]或是史迈德勒(B. Schmeidler)的论证,都不能动摇我。[106]实际上,贝娄只是指出人们之前已经知晓的毫无争议的事实(如宗教改革时代是一个重大转折),但是关于我所说的“首要的错误问题”,即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解答路德究竟属于“中世纪”还是属于“近代”这一问题,贝娄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作出反驳。
史学家之所以乐意相信分期构造的“客观性”,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存在,正如宗教改革时期或法国大革命;第二,特定、稳固的现实情况的清晰序列。没有人会争论这两点。但是,首先,我们并不能简单从“对应面”中得出对单个“时代转折”和其时代总次序的重要性的估计,这种估计只会在历史判决的立场受限性中产生。其次,现实情况的次序,如语言史的阶段,在无数纷杂短暂的过渡时期中发生,我们并不能简单从客体中得到分期,而这样一种现状(如语言史)也并不能成为划定历史发展其余所有次序的标准。我们若相信,凭借中古高地德语就能证明“中世纪”的“存在”,那就低估了分期问题的复杂性。[107]史学只能描述单个的而非整体的“发展”。
这个人们在1900年前后处理过的发展概念在部分情况下模糊不定,尽管如此,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并得到修正的新概念替代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领域中的“进化论”已经被战胜了。如果说发展概念严格来讲只能形象地应用于历史领域,那么毫无疑问,所有历史事物纷繁变化的事实会继续存在。万物变化的历史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绝对没有被抹除,反而更加清晰。曼海姆有这样的论述:
如果一个更早时期的哲学家,比如柏拉图、奥古斯丁或者库萨,断定了与如今论题有关的事物,那么,细加观察会发现,他们指的其实是其他的事物,因为存在于他们体系和生活总体中的每一句话、每一种思考形式必然有一种不同的功能,而这一功能一定导向一种不同的意义。(页20)
……
只有词语描述的相对刚性可以遮蔽如下事实,即在这些词语描述的背后,其所指的意义永远发生着变化。更近一步,每一个词语的历史实现都是不同的。人们不能说,在每一个“时代”,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得到了保存:它们只是以不同的分组、重读和细微区别在不同的时代出现,总是寻求通过保持一种相对“常量”而限制发展思想。然而,这些“本质性问题”从不消失,它们总是带着新的内容、新的中心和新的功能性意义重新降临。(页 35)[108]
此外,过去十年的史学家与前人相比,在更高的程度上学习了如何观察历史距离。尼采对于历史距离的感觉尤其敏锐,他将其描述为“最伟大的变化”:
万物的光亮和颜色都改变了!我们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古人对日常最熟悉的事物的感知,例如白天从睡梦中醒来;因为古人相信梦境,清醒的生活便有不同的光线,于是整个生命都带上了死亡及其意义的反射:“死亡”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死亡。所有的经历都以不同的方式朗现,因为有一尊神从它们之中闪现。一切决断和对遥远未来的展望也是如此,因为人们拥有神谕和神秘的暗示,并相信预言。“真相”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因为迷狂者曾是它的口舌——这使我们毛骨悚然或哈哈大笑。每一种不公正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感觉,因为人们不只惧怕公民的惩罚和侮辱,更害怕神的报复。
人们对魔鬼和引诱者的信仰,不是时代的欢乐又是什么!人们在近处看到魔鬼的潜伏,这是何等的激情!当质疑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罪行,是对永恒之爱的亵渎和对一切美好、崇高、纯粹和仁慈事物的不信任,这是怎样的哲学! 我们将万物重新着色,我们不断地在万物上涂抹勾画——但面对那些大师和古老人类的斑斓绚丽的色彩,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109]
4.内在与超越
凭借上述内容,我们是否已经可以测定历史思考的领域?或者说,史学家在此基础上能否以某种方式进入事物的“深度”,并断定事物原本的内容、实体、本质、思想、形态和意义?他能否进入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领域?如果这一切都可行,那么我们又应该在何种意义上讨论超越与形而上?由此,我们就来到了论述的最后一个要点。
对历史事物“本质”的发问早在19世纪就已经进入专业史学的视野——只要唯心主义哲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就不会陌生。这个时代的人们并不是在绝缘状态中从事单一科学学科的研究,而是希望在其与哲学问题的关联中表达它们。除了黑格尔之外,教会史学家鲍威尔最为强烈地肯定哲学与历史书写的紧密联系,在他眼中,历史与哲学的联系来自这一事实,即教会史可以在其历史发展中展示出基督教的本质。对于鲍威尔而言,历史就是杰出意义上的“批判”,是精神对其过去的思考行为。精神自身“从历史客观性返回到意识主观性中,通过意识到作为精神过程的外在历史过程(客观意义上的历史)”,它认识到“此过程中它自身的本质”:
在批判中,史学自身成了历史的哲学。[110]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经验科学的出现和哲学冥想的消退,本质问题与其他来自唯心主义哲学的要点一起,在历史科学的内部消退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历史主义危机恶化之前的时代,我们仍会遭遇这一对“本质”的发问。
教会历史书写的另一个例子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关于基督教本质(1900)的讲座。但1900年前后的时代特征却表明,事物的“本质”问题大多是一种“特殊任务”:这一任务在原本的史学工作之外,且并不能丰富原本的史学工作。人们在大多情况下认为,本质问题是一个系统性任务,它既不引起史学家的兴趣,也不阻碍他们的工作。此后,一种对于本质研究及其与史学的联结甚至统一的高涨情绪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种以“哲学”或“精神历史”为导向的史学出现了。
科学的主要倡议者是狄尔泰和特洛尔奇,前者带来的影响虽迟却十分强烈,后者则最为强劲地要克服在德国盛行的一种片面、非哲学的史学,这种史学的目标是对历史细节材料的准确加工和汇编。同时,诗人格奥尔格的圈子,尤其是贡多尔夫,艺术史学家德沃夏克(Dvorak)和斯特泽高斯基(Strzygowski),还有现代形态学家如斯宾格勒以及所有这些主要人物的后继者,都进入了我们的视域;我们在概述历史主义危机的症候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趋势的拓展,在这里,这种趋势的单一现象被视为众所周知的前提。总之,这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史学与哲学及艺术倾向的联结。
尽管如此,我们面对的是难以概览的纷杂问题和更为纷杂的解决它们的尝试。如果这个总体的科学问题得到重视,那么针对这一历史哲学运动的每一位领导者,和每一个处于这场运动中的重要科学概念,我们都需要开展特别的研究。在本文所涉及的范围内,我们只确定这一问题:这一运动是否真正撼动或克服了在历史主义危机出现之前流行的历史书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的角度观察这一运动:
(1)按照它们的普遍倾向(历史与哲学的联系);
(2)按照它们的特殊方法(直觉);
(3)按照它们的特殊对象(“形态”“本质”“理念”“意义”等等)。
这里的批判性意见当然只涉及运动的部分领导者。
(1)普遍倾向。这种现代的、以历史哲学为导向的倾向,第一眼看上去仿佛与历史书写的先前阶段处于一种极端的对立中,新旧理论的拥护者自然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对立。我们只需回忆布克哈特的判断:历史哲学是“半人半马,是一种矛盾”,因为“[历史]是协调,是非哲学,哲学是从属,是非历史”。[111]众所周知,我们必须谨慎地评判“世界史观”:
我们不能忘记,印刷文本是二手文本,而原始手稿有一种临时性质,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作品的新全集并没有被印制出来。[112]
作为比布克哈特年轻的同代人,法国史学家古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常说:“存在一种哲学,存在一种历史,但不存在历史的哲学。”[113]这种19世纪的表达背后存在着一个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这两位学者都希望通过他们的前沿观点表达出真理,而要求史学拥有更强烈的哲学气质的现代倾向同样如此。
事实上,这种哲学气质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在史学中存在——即使是在反对哲学、看似纯粹的经验史学时代也是如此。丹纳(Hippolyte Taine)——他将自己视为一位准确且纯粹按照经验行事的史学家——在《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中对此有许多富有思想性的论断。我在前文已经论述,在我们的精神切入一切历史形象时,一种系统化的要点已经存在了;人们在历史主义危机恶化前极大地忽略了这一要点,而现代历史逻辑却清晰地证明了它的存在。这样一来,1900年前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书写与现代以历史哲学为导向的(或者至少带有历史哲学感觉的)史学之间的对立,对于双方支持者的认知而言,就比实际上的更极端,只是这一区别并不明显。
人们可以争论哲学特征应该并可以拥有的长处。“哲学”一词是如此多义,我们关于这种哲学特征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这完全不是在现代历史哲学倾向中产生影响的某种特定哲学,实际上,对历史材料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当代哲学意见的丰富性与混乱性。此外,这种哲学特征在不同的史学家及其不同的著作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强度。如果把迈内克的《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中的哲学元素与意大利人克罗齐的历史书写中的哲学元素相比较,我们就能马上看出区别:在迈内克那里,哲学元素是政治历史的一种思想史深化,它澄清了与其思想相适应的背景;而在克罗齐那里,哲学元素则是一种理论和一种历史实践,根据这一实践,哲学和历史思考是同时发生的。而在韦伯对历史“理想型”的加工方法[114]那里,这种哲学特征的种类和范围又有所不同。上述三个人都会对1900年“实证主义”或者以“实证主义”为立场的史学家感到诧异。
但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谨慎地讲,这一探索史学和哲学之间的更紧密感觉的倾向,一定包含其合理性,正是这种强烈的合理性使该倾向自身得以实现。首先,史学家若不想仅仅成为一个技师,就必须熟悉历史逻辑(历史认识)问题;其次,一个人只有在其思考对象的广大关联和内部深度中观察对象,才能真正从历史角度思考这对象。这一倾向纠正了1900年前后看似在准确事实领域内保持不变的片面、反哲学的史学,也已经完全处于一百多年前那些伟大的唯心主义历史理论家所追求的道路上。我只需提及洪堡,或者是之前已经提到的教会史学家鲍威尔,后者有这样一句名言:
如果没有哲学,历史对我来说就永远是死的、是沉默的。[115]
必须存在一种主要关注外在事实的历史书写,这当然无可争辩,这本应是历史书写的一种完全合理的分支。但在历史主义危机中,这种对于事实史的兴趣被削弱甚至成为背景,成了对强调“本质”“形态”和“理念”的浪潮的补充。这种主要以事实和事实关联为目标的历史科学分支将会一直保持下去。即使被遏制,它也会在自身的存在中得到保存。
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以这种方式书写“世界历史”、文学史或教会历史等等,否则,我们就是把事实揉成一团,其结果也并不是实际的历史,而是经院哲学,是对书本知识的堆砌。将这些事实聚合和组织起来的,不是它们与一种主导思想的坚实而清晰的关系,而是对年代顺序和某些时空框架(如“德国”或“地中海”)的移除。而就一种带有更强哲学特征的历史而言,科勒(Walther Köhler)以更有力的决断登场了。[116]
辛兹(Otto Hintze)也说道:
……正如专业哲学家一样,专业史学家可能并不缺少由哲学精神实现的历史观察。[117]
我并不承认格奥尔格圈子的所有作品都是真正“史学的”。我在上文已经做出必要阐述:在这些大多俏皮风趣的作品中,一种在完全的广度中以“对应面”为导向并严格与其联结的历史书写,与理念联想式的论证——“神话”或“传奇”等等——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此外,这些作品中对于真实史学的深思熟虑,大部分是违背了原本史学精神的统计性内容。即使不考虑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已经可以说,格奥尔格圈子所使用的方法并不会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因为这种方法只能应用于相对较少的“形象”,大多数的历史尺度与这种“神的授予”相距甚远。
关于现代的历史哲学倾向和这一倾向的合理性,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在这里,我并不打算更详尽地处理历史书写与艺术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并不直接与上文所述的思想潮流有关,同时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尽管在危机时代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常常被模糊,一种广泛而本质性的一致洞见仍占据统治地位:艺术倾向并不能伪造原本的历史书写,而美学要点的共振也完全合理。一种充满活力的美学要点就可能存在于一件严格哲学系统化的作品的构筑原理内部:它并不会带来危险,反而会增强表达本身的刺激、清晰和让人印象深刻。处于历史书写中的艺术要点绝不会被驱逐出历史书写,只是,我们不能混淆一种偏离为小说的历史书写与一种严格在科学判定之中保持自身的历史书写之间的界限。[118]
(2)而这种新倾向的许多拥护者使用的特殊方法又是怎样的呢?单个拥护者的方法之间当然存在细微差别,然而,我们同样无法归纳出一种普遍性特征。这种方法是直觉性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握并呈现直觉这一相当复杂的概念。[119]以下是一些暗示。就根本而言,直觉的概念非常重要,因此,人们近来对其意义的重新强调非常有益。它总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知识并不完全是一种对被感知事物的描摹,我们同样要意识到直觉的本质和界限。直觉在启迪层面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我们必须对历史材料进行不间断的处理才能持续地控制直觉。直觉必须保持与这种处理工作的持续接触,但同时也不能被引入纯粹幻想的领域。[120]此外,要求人们通过直觉达到事物形而上的本质核心,通过“本质观”达到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超历史性和形而上性,这样的思想必须予以明确拒绝。
(3)最后一个问题关涉这里所讨论的史学的特殊对象,即事物的“理念”“本质”“形态”或者“意义”,以及其他的常用表达。一般而言,这其中的每个概念在现代哲学性的历史思想家那里,都有一种非常精细的、带有个体化差异的用法。例如“形态”一词,它在柏拉图“理念”的意义上与浪漫主义一同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逻各斯”的意义上则被理解为“形式”等等。以相同的方式处理甚至否决所有这些概念不啻一种强暴。然而,我们无须更细致地处理单个概念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凭借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如“本质”,我们能否真正进入严格意义上的超越,并克服1900年的史学的根本内在性呢?
为了避免颠倒逻辑次序,我们应首先阐明史学的根本内在性这一概念。“内在”和“超越”是两个意义波动很大的概念。想要处理它们,必须准确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当史学家的立场被解释为“奇迹报告”时,我们常常在历史论证内部观察到这两者。我在这里并不讨论这一问题——它虽一直在神学和神学史学内部起到重要作用,但与此处待论证的问题并不相同。这个“奇迹问题”是:超越性能否在事件的特定层面上延伸入内在?而对于可以通过普遍的人类经验手段得到判定的事物而言,它们的领域和关联在特定的位置上能否得到连续的思考?与上述问题相反,我们在这里希望回答的问题是:处于普遍人类经验的关联之上(über)或之后(hinter)的、 “本质观”所能够进入的事物,能否被我们观察到?
即使在界定之后,“内在的”和“超越的”这两个概念仍不能判定为完全单义。仍存在一种内部的超越性:这一超越性存在于可能的人类经验领域内部,即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于“内在性”内部;通过它,我们超越了纯粹的“自然”。从纯粹的外部“自然”即感官所感知的世界观察,在我们思维中发生的每一种过程都是“超越的”。
我在第二章描述了历史思考时发生在我们思维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相对于在“经验”角度下的历史来源材料是“超越的”。作为经验科学的史学的常规描述不能遮蔽这一事实。这一描述得到广泛传播也容易理解。在自然科学占据优势的时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科描述为一种经验科学以维护其合法性。在历史主义危机期间及之后,面对现代历史哲学倾向和其他现象,为了划清史学与诗学以及形而上学的界限,这一描述又得到了重视。
如今,我们不能因为上述浪潮已经过去就反对这一描述。如果我们想到康德对经验知识的描述——“源于经验,即在经验中拥有”,仅“通过经验才成为可能”,“通过感知确定一个客体”——[121]那么,历史科学就是一种经验科学,而绝不是纯粹推理或冥想的科学。但这也取决于严格表达的经验性事物在历史思考内部能够延展多远。史学是经验的,因为“感知确定客体”,但这绝不表示客体自身仿佛能够被经验性地感知。历史科学的对象恰恰不处于感官可感知的状态。历史科学只以经验性事物为前提,其来源——文本、图像、建筑、笔记等等,都是以经验性的方式存在的。
史学在这一经验性层面上甚至有——但也仅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对文本的阅读没有一次是在纯粹经验性、在感官可感知状态的纯粹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的。严格意义上,纯粹经验性的阅读只能确定文本的字母。但即使我可以纯粹经验性地确定 [义人必因信得生],以纯粹经验性的方式得以实现的事物也同时被穷尽了。我根本不能纯粹经验性地确定,
[义人必因信得生],以纯粹经验性的方式得以实现的事物也同时被穷尽了。我根本不能纯粹经验性地确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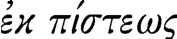 [因信]与
[因信]与 [义人]还是
[义人]还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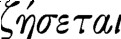 [得救]黏得更紧。严格的经验性和超经验性在历史思考中进入彼此。正如我超越了对当下文本字母的确定并尝试理解被传达的句子一样,当我要翻译《罗马书》一个完整的段落,或要给出使徒保罗的性格描写或者展示他的神学时,我就超越了在严格经验意义上可被证明的事物的界限。如果人们以常规的方式将史学描绘为一种经验科学,却没有同时说明历史思路内部严格经验性处理方法的有效范围非常受限,那么,历史和唯物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别就会相当显著——比实际的情况更加显著。
[得救]黏得更紧。严格的经验性和超经验性在历史思考中进入彼此。正如我超越了对当下文本字母的确定并尝试理解被传达的句子一样,当我要翻译《罗马书》一个完整的段落,或要给出使徒保罗的性格描写或者展示他的神学时,我就超越了在严格经验意义上可被证明的事物的界限。如果人们以常规的方式将史学描绘为一种经验科学,却没有同时说明历史思路内部严格经验性处理方法的有效范围非常受限,那么,历史和唯物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别就会相当显著——比实际的情况更加显著。
表面上看,当我谈论宗教改革的“理念”或描述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的进程时,我仿佛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运动——两者像是完全处于不同的层级。然而,深层的观察表明,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我们思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谈论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时,我塑造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思想总体。正如磁铁吸引铁屑,“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这一历史主题使得从属于它的历史元素都流动起来。这些被研究激发出来的历史元素在我的精神中出现,并作为“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的历史思考形象贯穿了我的思考。同时,这些元素处于一种与“对应面”的特定逻辑关系中,并从中获得了针对错误塑造的修正。另一方面,当我谈论宗教改革的“理念”时,从形式上观察,在我精神中发生的是完全相同的事件:一种特定的历史思想总体形成并处于一种与“对应面”的特定关系中,并从中获得对错误塑造的修正。
在这两次思考中,我都通过涵盖性概念来把握“对应面”,只是概念有不同的范围——形象地说,不同的概念涵盖了对应面这一概念大小不同的“表面”。从一种处理方式向另一种处理方式的过渡,并不代表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别的过渡;在这其中存在无数的中间形式,这些中间形式使得我们不能鲜明地区分这两种处理方式。因此,我们不能将“内在的”和“超越的”直接对应为这两种处理方式。我们不能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这一历史形象是“历史的”,而宗教改革的“理念”是“形而上的”,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超越的”。事实是,两者在一种意义上都是内在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也都是超越的。
内在与超越在形式结构方面都由涵盖性概念组成,因而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两个总体也并非形成于我们历史思考精神中的两个不同源头,而是均发源于使“对应面”成为历史描述的推动力,正如两者都在我们精神中出现,没有任何事物偏离这一过程。我们能够使“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这一历史形象在我们思维中出现,并不令人惊异——这类似于日常实际生活中在我们思维中产生的相似的精神形象。而即使我们思考宗教改革的“理念”或“本质”,也没有任何神秘的、启发性的事物在我们思维中产生。这种“理念”更多是在特定情况的强制下形成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教派战争的时代之后如何谈论基督教的“本质”。
对于上述其他的概念,如“意义”“形态”等,也有相似的证据。所有这些概念与第一种历史形象一样,都不能使我们更加靠近“对应面”。但这些概念将我们带入一种“更伟大”的深度——在这种合理的形象化表达背后,我们其实是在说,对于我们而言,一种历史尺度的精神“内容”比对历史单个进程的描绘更有价值。但这一“深度”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形而上的。因此,“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将我们引入形而上领域”的说法并不清晰,也应该加以规避。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对事物的思想史或精神史的处理,不能克服在1900年前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书写或使其成为多余,与此相反,这一处理只能补充和充实后者。
结 语
我们刚刚论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凭借对历史“理念”的塑造,向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领域推进?这不等同于问: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更不是在问:是否存在一种“形而上领域”?尝试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领域的冥想思考在近年得到了显著增强。我若要处理现代历史哲学,就必须处理近代神学家解答“上帝与历史”的问题[122]、解决基督教的历史形而上学问题或“基督教历史神学”问题[123]的努力,我也必须处理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Berdjajew)[124]关于历史意义的作品或斯坦纳式的人类学冥想。但这一切都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外。
回顾全篇,需要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在1900年前后占据支配地位的对史学建构的把握,及其与思考历史的精神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纠正。对具有单义、已完成结构的“对应面”的想象,用舍勒的话说,[125]就是加密形而上学(Krypto metaphysik)。这一观点的持有者并没有意识到,该观点在本质上是对历史事物的一种神化,这种神化与在所谓的一元论或自然科学世界观中对“自然”的神化相似,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当代史对照。神像被捣毁,不能再次拼合。历史事物的绝对表达(“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被“流动的过去”所代替。于是,在历史主义危机恶化之前普遍适用的一大重要理论前提被撼动了。
第二,历史尺度在其关联中被前后一致地排列,相对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得到保持和加强。
第三,历史发展观在其本质表达中是合理但受限的。但是,对时代区别以及对人类事物永恒流动及变化本质的认识保持下来,并在特定的方面得到深化。
第四,在“内在”领域及事实领域保持不变的史学得到了思想史、本质观和相似方法的补充。于是,“内在—超越”这组概念带来的问题得到精炼。一种存在于内在性内部的超越性被开拓出来,但这绝对不是对于史学的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领域的突破。
在这四个互相关联的要点中,第一点和第四点最为重要。与1900年的历史书写相关联的是世界观要点,而经由历史主义危机,这些要点部分被废除,部分得到了改造。但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种明确地与所有系统性思考分离的史学并不存在。史学与系统性思考并不处于敌对的二元论或无关紧要的对立关系中,事实上,如果没有互相的关联,我们根本无法思考这两者。一种决定性的新方向已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