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艺术吗?
电影无疑是20世纪人类创造的最大奇迹之一,它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图像连续放映在银幕上,使之看起来像实在活动的形象,它将技术手段与叙事因子结合在一起,永不厌倦地为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世俗神话。20世纪以前,让人们在特定时间内,集体进入一间硕大的黑屋子,沉浸在那些由活动的影像编织而成的虚幻世界中,是一件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进入20世纪后,这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影方式。电影几乎将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传统艺术之美尽数为己所用,并覆盖和取代了这些传统艺术的社会地位和基本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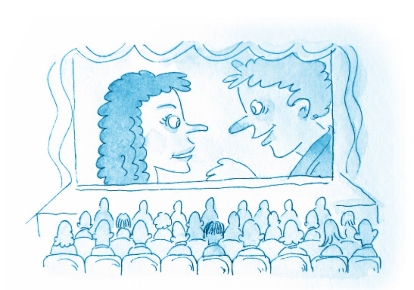
电影是人类创造的最大奇迹之一
作为20世纪的新生事物,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瞩目同时也备受争议。人们对它的思考和评价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持全盘否定的批判态度。电影诞生不久,便出现了“梦幻工厂”的命名,这意味着电影被视为一个生产白日梦的工业系统,它不断引导人们进入虚假的美梦和许诺中,暂时忘却了生存的苦难和现实的不公,继而逐渐丧失了反抗意识,以致被主流意识形态同化或整合。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与电影工业联姻,推出一个又一个纵情声色的娱乐片,使人们在反复的感官刺激中变得心灵麻木、安于现状,因此一部分电影理论家将电影视为邪恶的艺术,认为它诞生的那一天应该受到诅咒。有关电影的“致幻”功能,曾有人将它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相类比。这则寓言是这样的:有一群囚犯居住在洞穴中,双腿和脖子都被锁住,不能回头,也无法移动。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被迫面朝着洞穴深处,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在他们背后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于是在洞穴外面走过的人群就会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洞穴深处的墙壁上。由于这群在洞穴中长大的人从来没有见识过真实的世界,于是就把这些影子当成唯一的真实。终于有一天一个人挣脱了枷锁,跑到洞口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才让自己从影子的幻觉中走出来。当他返回洞穴向其他人解释真实的世界时,遭到了那些同伴的奚落,他们依然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墙上的影子外,再无其他真实的东西了。这则千年之前的神奇寓言似乎是专门为电影准备的,其表述方式和寓意均与电影的放映及观赏模式深刻契合。人们坐在电影院面朝银幕,好比洞穴中的囚犯面对眼前的白墙;强光从观众背后将影像投射到银幕上,一如那堆篝火将真实事物的影子映照在囚犯眼前的白墙上;观众对光影世界的迷恋,就像囚犯对墙上影子的认同。因此电影的蒙太奇世界是一个制造幻觉、远离真实的梦工厂,其社会功能是使人们在破碎的现实中获得想象性的抚慰和满足。
围绕电影的另一种评价,是对伴随电影而来的新技术持乐观主义态度。本雅明就属于这一类,尽管作为一个充满贵族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对有光韵的传统艺术始终充满眷恋,而且也十分清楚电影本身的缺陷,然而他不以顽固保守的姿态来衡量新生事物,相反他的艺术观念十分开放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辩证法:既然电影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在它与生俱来的缺陷背后也必然隐藏着积极进步的因素,那么充分了解它,挖掘其潜在的革命功能将是一件比抱怨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说同时代的理论家还在争论着电影算不算艺术,拼命为电影注入膜拜价值以正其名,那么本雅明已远远走在了他们前面。通过考察电影对传统艺术的冲击,他指出,电影以自身的展示价值压倒了传统艺术的膜拜价值,传统艺术将在光韵的消逝中寿终正寝;电影打破了文化精英对艺术的垄断,使更广泛的大众参与到艺术中来,通过对大众的宣传和动员,发挥电影的政治组织功能;电影技巧若被先锋派艺术家有效利用,将成为人们反抗甚至颠覆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有力武器;电影拓宽了人类视觉和听觉的感知范围,以其自身的技术手段捕捉到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从而启示人们去关注心灵深处的无意识世界。本雅明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并不新鲜,然而在20世纪上半期却具有石破天惊的开创意义,他对技术的推崇曾遭到过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多人的批评和误解。当然本雅明的激进立场与当时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不无关联,抛开这些不说,单就他思考技术问题的角度而言,依然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走过20世纪,电影发展的历史也已超过100年,回顾一下电影是否如某些保守派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扼杀想象、麻醉心灵,把人们囚禁在一个物质和表象的世界呢?事实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凭借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可以处理人类自有史以来一切高深玄妙的命题,他们以摄影机为笔,描绘了一幅幅充满原创性和想象力的动人画卷,在此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这些电影大师的名字: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帕索里尼、基耶斯洛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