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继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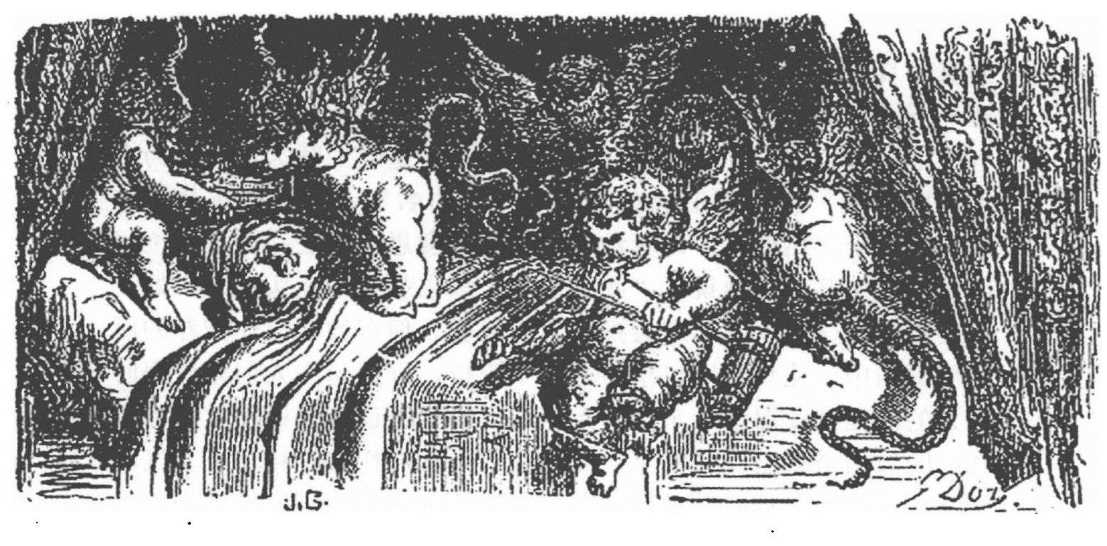
当年巴黎圣母院里有一位上年纪的议事司铎,他在圣彼得牛头教堂附近置办了一间舒适的居所,而且就住在那里。这位议事司铎刚来巴黎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教士,就像一把没有剑鞘的佩剑。不过,他长得仪表堂堂,又多才多艺,而且体格健壮,有时即使干好几个人的活也不觉得累,因此深得女信徒的喜爱。他一门心思要为夫人们做忏悔:为心情抑郁的夫人送去温柔的宽慰,为病恹恹的女士奉送少许自制的芳香药膏,为所有来做忏悔的夫人送上一枚糖果。他因待人谨慎,积德行善,并具备教士应有的其他品德而名扬巴黎城,甚至还去宫廷里为贵夫人们做忏悔。那时,为了不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嫉妒,为了不让丈夫们及其他人看着眼红,总之为了给这种积德行善、有利可图的事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德盖尔德元帅将圣维克多的遗骨送给他,凭借这件圣物,议事司铎创下的所有奇迹也就功德圆满了。要是有好奇的人打听他的事,那么准会得到这样的答复:“他有一根包治百病的圣骨。”针对这个说法,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因为圣物的功效是毋庸置疑的。在教士的长袍之下,这位好心的神甫还有一件久负盛名的宝贝,这是勇猛的骑士面对真刀真枪毫不退缩的宝贝。因此他的日子过得就像国王一样,挥洒一下圣水刷子就能造出金币来,须臾间就能将圣水变成美酒。此外,他还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公证人证书及遗嘱上睡大觉,因为有人隐瞒真相,在遗嘱追加条款上写上他的名字,“追加条款”这个词起源于“尾部”,即表示遗赠零头的意思。总之,要是这位好心的修道士开玩笑地说:“我真想拿一顶主教冠戴在头顶上,好让脑袋更暖和一点”,他准会推选为大主教。但在教会向他推荐的所有俸禄当中,他只选中议事司铎这个职位,好把为夫人们做忏悔时得到的好处继续保留下来。一天,这位勇猛的议事司铎感觉肾亏腰软,因为他毕竟已经68岁了,而且在听夫人们忏悔时耗尽了元气。于是,他回忆起自己做过的所有善事,感觉可以把布道传教的圣事停下来了,况且凭借自己的血汗,已挣下十万金币的家产。从那天起,他只给地位显赫的贵夫人们做忏悔,而且做得尽职尽责。于是,宫廷里的人都说,虽然优秀的年轻修士们身手不凡,但唯独圣彼得牛头教堂的议事司铎能为高贵的夫人洗刷灵魂。后来,议事司铎仰仗自然之力成为满头鹤发的九旬老翁,虽然双手有些颤抖,但腰板依然十分硬朗;他过去不咳嗽的时候也常常吐痰,现在却是咳嗽的时候也吐不出痰来;他过去出于仁爱之心,频频起身向信女们施礼,现在却坐在椅子上,懒得站起来。但他依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言不发,表面看上去依然是圣母院富有活力的议事司铎。由于这位议事司铎好静厌动,有关他生活放荡,与人交欢的传闻开始在平民百姓当中流传开来,这些平民百姓都是无知的粗人。他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不过却不问世事,过着隐居的生活,也许还由于其他说来话长的往事,有些人竟说,真正的议事司铎早在50年前就去世了,现在是魔鬼依附在这修士的身上,他们这么说无非是显示自己多么了不起,同时要败坏我们圣教的名声。实际上,曾在他那儿做过忏悔的女士们回想起往事时,都还记得她们确实如愿以偿地从神甫那里得到神秘的圣水,恐怕只有魔鬼才能以极大的热能化解出这么多圣水来,因此她们也觉得魔鬼真是依附在议事司铎身上了。但这个魔鬼已被她们折磨得筋疲力尽,即使碰上一位20岁的妙龄公主,他也懒得动弹了。无论是有理智的贤者,还是见多识广的人,或是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的资产者,这些人总能在秃头上找到虱子,他们都在琢磨,为什么魔鬼要披着议事司铎这身外衣去圣母院呢,为什么非要和其他议事司铎一起去教堂冒险呢,甚至大口地吸着香炉里飘出的香气,品尝圣水的滋味,还做着其他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针对这些奇谈怪论,有人说魔鬼兴许也想脱胎换骨,皈依宗教;也有人说魔鬼举手投足都在模仿议事司铎的样子,就为了嘲弄这位善良的听忏悔神甫的三个外甥,他们是神甫的财产继承人,魔鬼故意让他们等待,等他们自己都死了也得不到舅舅的这笔丰厚的遗产。他们每天都去看舅舅,看他是否还睁着眼睛,事实上,每次见到他,他们都感觉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富有活力,还带着一股挑逗的意味,就像蛇怪的厉眼,他们见他这副样子感觉很快活,因为他们很爱舅舅,虽然这爱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到这一点,有一位老妇人信誓旦旦地声称,议事司铎就是魔鬼,因为有一天议事司铎到赦罪院主教家里做客,吃过晚饭之后,他的两个外甥带着舅舅往回走,一个外甥是诉讼代理人,另一个是长枪队长,他们既不拿手提灯,也不点灯笼,结果不小心让议事司铎撞在了为建造圣克里斯多夫雕像而码放的石头堆上。外甥们赶紧到旁边老妇人家里去借火把,而老人倒下的时候先是冒出火来,接着在外甥们的呼喊声中,在这位老妇人火把的照明下,老人竟稳稳地站在原地,腰杆笔直,心情快活,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灰背凖。他说是赦罪院主教的好酒给他勇气,来承受这个打击,而他的老骨头依然十分硬朗,这把老骨头曾经受过比这次撞击还猛烈的攻击。好心的外甥们还以为他被撞死了呢,见他站在那里大为吃惊,这才意识到时间都不能轻易地扳倒他们的舅舅,在这个行当里,连石头都拿他没办法。因此,管他叫好舅舅总是没错,因为他的身子板真是棒。有些嚼舌头的人说,议事司铎在他往来的路上总会碰上许多石头,于是便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以免再撞上石头,况且他担心发生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才过上隐居的生活。
总之,不管这些闲言碎语以及种种传闻是真是假,也不管魔鬼是否依附在这位年迈的议事司铎身上,他一直待在自己家里,不肯死去,和三位继承人一起生活,就像和自己的坐骨神经痛、腰痛以及其他折磨人的病痛共处一样。这三个继承人当中,有一个是最恶劣的兵痞,他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时候,一定撕破了母亲的肌肤,因为他生出来时就长了牙齿和毛发。他过日子只图眼前痛快,甚至不惜寅吃卯粮,他身边还守着几个放荡的女人,甚至给她们买网状发饰。他有耐力,有力气,也会尽情地享受,这些都像他舅舅。在激烈搏杀的战场上,他尽力去打击对手的头部、肩部,而不让自己受伤,这是在战场上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他在搏斗时从不惜力,事实上,除了骁勇之外,他没有其他美德,但还是被任命为长枪队的队长,深受勃艮第公爵的赏识,而公爵对自己的部下究竟干些什么勾当却很少过问。这个外甥名叫科谢格吕,而那些债主、门房、资产者以及所有被他搜刮的人都叫他“恶猴”,因为他既狡猾又强壮,不过他天生就是驼背,但千万别以看得更远为借口爬到他后背上去,否则他会给你点颜色看看。
第二个外甥曾学习过惯例法则,凭借舅舅的庇护当上了诉讼代理人,在法院里为当事人出庭辩护,他的委托人大多是曾在议事司铎那里做过忏悔的女士。他和当长枪队长的哥哥都姓科谢格吕,但别人为了嘲讽他,给他起了一个“皮耶格吕”的绰号[1]。皮耶格吕身体孱弱,浑身似乎总是在冒冷汗,面色苍白,那副嘴脸就像一只石貂,不过他比长枪队长哥哥还强一点,对舅舅还有一点点爱心。但是,近两年来,他那颗爱心出现了裂痕,他的感激之情也渐渐地消失了,因此每逢阴天潮湿的日子,他就喜欢套上舅舅的长裤,提前去压榨这笔丰厚的遗产。
他和兵痞哥哥总觉得分割给他们兄弟俩的遗产太少了,因为无论是从公正的角度,还是从权益、事实、司法、本质及实际情况看,都应该将全部财产的1/3分给一个穷表兄弟,这是议事司铎另一个妹妹的孩子,他也是遗产继承人,一直在楠泰尔附近的田野里放羊,但老人并不怎么喜欢他。
这个羊倌不过是个普通农民,他听从两位表兄的劝告,来到城里,表兄让他和舅舅住在一起,希望他这个愚昧无知的家伙干下什么蠢事,让议事司铎讨厌他,好把他从遗嘱里赶出去,羊倌不但粗俗,而且不谙人情世故,人也显得很愚笨。于是,这个名叫希贡的可怜羊倌便独自和舅舅住在一起,住上一个月之后,他倒觉得看护一个教士比看一群羊更有趣,还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他甘愿成为议事司铎的家犬、仆人和拐杖。听到老人放个屁,他就说:“愿天主保佑您!”见老人打个喷嚏,他就说:“愿天主拯救您的灵魂!”老人要是打个饱嗝,他就说:“愿天主守护您!”他要么出去瞧瞧下雨了没有,要么就看看那只母猫跑到哪儿去了,整天少说多听,替老人擦鼻涕,把他当作这世上最出色的议事司铎来崇拜。他全心全意做着这一切,对老人更是坦诚相待,不知道自己是在奉承老人,宛如母猫舔舐刚出生的小猫。做舅舅的当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面包的哪一面抹上了黄油果酱,经常嫌弃可怜的希贡,随意支使他,就像摆弄一个骰子,直呼他的名字,对他呼来喝去,而且总是对另外两个外甥说,希贡真是太笨了,这会让他死得快点。闻听此言,希贡更加勤奋地服侍舅舅,好让他满意,但无奈他天生长着两条短腿,短得像西葫芦,宽肩膀,粗胳膊,动作也不灵活,他这副长相更像西勒诺斯,而不像泽费罗斯[2]。事实上,可怜的羊倌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民,不可能再去塑造自己,况且他又长得很肥胖,只有等继承到遗产之后再去减肥了。
一天晚上,议事司铎先生谈论起魔鬼的境况,谈论起天主为下地狱者设置了种种精神折磨和酷刑,善良的希贡睁大眼睛在旁边听着,眼睛睁得大如炉口,但根本不相信舅舅说的这些话。
“喂,”议事司铎说,“难道你不是基督徒吗?”
“当然是啊!”希贡答道。
“那么既然能给善人安排一个天堂,难道不应该给恶人准备一个地狱吗?”
“当然应该,议事司铎先生,可这根本用不着魔鬼呀……假如您造出一个恶人,把您搅得天翻地覆,难道您就不会把他赶出去吗?”
“是的,希贡……”
“这就对了!我的舅舅先生,天主神奇地创造出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却容忍这么一个可恶的魔鬼把一切搅得一团糟,那么这个天主是不是缺心眼呢……呸!如果真有一个好心的天主的话,我就绝不相信会有魔鬼……您相信我说的没错。我倒真想见识一下魔鬼到底长什么样!……嘿!我才不怕他的爪子呢……”
“我要是相信你说的话,就不必担心自己年轻时做的事了,那时候,我每天要做十次忏悔……”
“那您还得继续忏悔,议事司铎先生!……我相信,等到了天堂,这就是您的宝贵功德。”
“嘿!嘿!是真的吗?”
“是的,议事司铎先生。”
“希贡,你不承认这世界上有魔鬼,难道就不怕吗?”
“在我看来,魔鬼就像是一捆稻草,根本不必害怕!”
“你这话说出去会让人讨厌的。”
“绝对不会!天主会保佑我不受魔鬼的侵袭,因为在相信天主方面,我比那些学者们更有学问,而且不像他们那么笨。”
两人正说着呢,另外两个外甥走进来,他们从议事司铎的口气中发现舅舅并不怨恨希贡,他对希贡的种种抱怨都是假装的,就是为了掩饰对希贡的情感,兄弟俩面面相觑,惊诧不已。接着,他们见舅舅又笑起来,便问道:
“假如碰巧要让您立遗嘱,您把房子留给谁呢?”
“留给希贡。”
“那么圣德尼街征收租税的地产呢?”
“留给希贡。”
“还有维勒帕里西的封地呢?”
“留给希贡。”
“这么说,所有这一切都要传给希贡了?”长枪队长扯着粗嗓门说道。
“不,”议事司铎微笑着答道,“虽然按规矩立遗嘱对我来说是有利的,但我的遗产最终会落在你们当中最精明的那个人手上。我能预见到未来,对你们每个人的命运都看得一清二楚。”
议事司铎这个老滑头朝希贡投去狡黠的一瞥,宛如一个风骚女人朝一个小白脸送去的秋波,好把他勾引到自己的淫窝里。这火辣辣的目光让羊倌茅塞顿开,从这时起,他不但有了悟性,而且心有灵犀,人变得机灵了,脑袋也开窍了,就像刚入过洞房的新娘。诉讼代理人和长枪队长却把这番话当作《福音书》里的预言,在向老人施礼之后,就转身告退,离开这里,对议事司铎那荒唐可笑的念头感到很郁闷。
“你觉得希贡怎么样?”皮耶格吕问“恶猴”。
“我觉得,我觉得,”兵痞低沉地吼道,“我真想埋伏在耶路撒冷街上,把他的脑袋揪下来,扔在他脚下,要想把头安上就让他自己安吧。”
“咳!咳!”诉讼代理人说,“你这种杀人手法很容易让人认出来,有人会说:‘一定是科谢格吕干的。’我倒想请他吃饭,饭后我们玩跳口袋游戏,就像在宫廷里玩的那种游戏一样,钻到麻袋里看谁跑得快。然后我们把他封在麻袋里,扔进塞纳河,请他去游泳……”
“这样他就必死无疑了。”兵痞接着说。
“那是!肯定得死。”诉讼代理人说,“表弟去见了阎王,遗产自然就归咱们俩了。”
“我当然愿意。”兵痞说,“咱们俩得合伙干,就像一个身子上的两条腿那样,因为你像丝绸似的那么精细,我如钢铁一般强硬,短剑和束带一样好使!……让你瞧瞧这个,我的好兄弟……”
“太好了!”诉讼代理人说,“就这么定了,到底是用麻绳,还是用短剑呢?”
“咳!还管那么多干嘛,我们要干掉的是国王吗?对付这么一个呆头呆脑的羊倌,还值得费这么多口舌……动手就行了!咱们俩要是谁最先让他脑袋搬家,谁就从遗产里多拿两千金币……我会诚心诚意地对他说:‘把你的脑袋捡起来吧。’”
“我会对他说:‘我的朋友,你游泳去吧!’”诉讼代理人笑着喊道,那副笑模样颇像短身上衣裂开的口子。
然后他们分头去吃晚饭,长枪队长去找他的姘头,诉讼代理人则朝他的情妇家奔去,他的情妇是一位金匠的老婆。
此时感到极为惊讶的是谁呢?是希贡!那两位表兄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边走边说,就像在教堂里向天主祈祷时那样口无遮拦,可怜的羊倌已听到他们在谈论怎么整死他。希贡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究竟是他们说的话飘起来了呢,还是自己的耳朵沉下去了。
“议事司铎先生,您听到了吗?”
“什么呀?”他说,“我只听见劈柴在火炉里冒水汽的声……”
“咳!咳!”希贡回应道,“虽然我一点也不相信魔鬼,可我还是相信我的守护神圣米歇尔,他在召唤我,我得赶过去……”
“我的孩子,去吧!”议事司铎说,“留神别掉进河里,也别让人割掉脑袋,因为我感觉听到流水声,况且街上的流氓无赖并不是最危险的……”
听到这些话,希贡感到十分惊愕,看了议事司铎一眼,见他神情高兴,目光炯炯有神,两脚呈钩状。此时他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得赶紧把这事处理掉,他想以后还有时间景仰这位高深莫测的议事司铎,有时间为他修剪指甲,于是,赶紧朝城里跑去,就像快步疾走去赶幽会的女人。
羊倌们在田野里经常会遭受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所以掌握了未卜先知的本领,这兄弟俩绝对想不到羊倌会有这种本事,常常在他面前密谋自己的好事,根本不把这位表弟放在眼里。
一天晚上,为了逗议事司铎开心,皮耶格吕便给他讲述自己是如何干金匠老婆的,不但让金匠戴上绿帽子,还在那顶绿帽子上刻上镂花,把那镂花擦得锃亮,再弄上几个小装饰,就像王子用的小盐瓶似的。听他这么一说,你倒感觉这个女子真像是一只兴奋的河蚌,与情人幽会时胆大妄为,趁着丈夫上楼的一会儿工夫,还敢和情人干一个回合,绝无惊慌失措的感觉,惬意地吞下情人那件宝贝,就像吞下一颗草莓似的。她心里只惦记着和情人亲热,总是吹毛求疵,做出愚蠢笨拙的事。她表面看起来很快活,颇像一个正直的女人,既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能让丈夫满意,丈夫像爱护自己的嗓子那样疼爱她,这女人像香水似的那么珍贵,况且五年来她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把自己的爱情也梳理得头头是道,从而赢得规矩女人的好名声,也赢得丈夫的信任,丈夫放心地把钱袋、家产都交给她打理。
“那你们什么时候吹笛子呢?”议事司铎问道。
“每天晚上。而且我还经常和她一起睡。”
“怎么睡呢?”议事司铎惊讶地问道。
“是这样。在她的寝室旁边有一间陋室,里面有一个大衣柜,我就躲在衣柜里,她丈夫每天晚上都去他的呢绒商朋友家吃晚饭,常常和呢绒商的老婆干那种事。等她丈夫回来的时候,我的情妇就推说身体不舒服,把他打发走,让他自己去睡,然后到放着大衣柜的这间陋室里来治病。第二天早晨,金匠去铺子里工作,我就趁机赶紧溜走。他们家那座宅子有两个出口,一个通向木桥,另一个通到街上,我总是从丈夫不走的那个门进来,借口要和他谈谈他委托我办的几场官司,这官司我一直拖着不结案。我不但让他戴绿帽子,还能从他那儿捞点进项,因为打官司的手续费和种种开销恐怕比养几匹马的花费还要高。他很喜欢我,就像所有戴绿帽子的人喜欢替他在维纳斯天然花园里勤耕细作的人一样,没有我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然而,他口若悬河地把这些丑事讲了一遍,没想到羊倌却将其记在心里,在这大难临头之际,总会有一丝亮光给羊倌指明方向,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为他指点迷津,其实每个动物都有那么一点点本能,足够维持到终生。于是,希贡便撒开双腿跑到百灵鸟街,金匠正和呢绒商的老婆在那儿吃晚饭,他使劲敲门,透过门上的格栅回应里面的盘问,声称自己赶来送信,有国家机密相告,他这才被让进呢绒商的家里。他开门见山,直奔这档子要事,将那位正在兴头上的金匠从饭桌前拉起,把他带到大厅一边,对他说:“假如您的某个邻居给您戴上绿帽子,这会儿有人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交给您,您会把他扔进河里吗?”
“太好了。”金匠说,“但要是您拿我耍着玩,可别怪我不客气。”
“嘿!嘿!”希贡接着说,“我是您的朋友,特意赶过来告诉您,您在这儿伺候呢绒商老婆多少回,皮耶格吕律师就服侍过您太太多少回,您现在要是赶回自己的店铺,准能看到一场好戏。等您到的时候,那位好心地帮您清扫那块地方的家伙,就会躲进大衣柜里,好让您看不出那块地方被清扫过,您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地方。现在我就指望您能让我把这个大衣柜买下来,我会赶着一辆马车,在桥头上等候您的吩咐。”
金匠穿上大衣,戴好帽子,二话不说,撇下呢绒商的老婆,疾步朝自己的老巢奔去,就像一只吃了老鼠药的耗子。他来到家门前,使劲敲门,里面的人打开屋门,他走进屋里,大步登上楼梯,见桌子上摆着两套餐具,又听见关大衣柜门的声音,这时才见他妻子从偷情的房子里走出来,他随即说道:“我的心肝,这里怎么摆着两套餐具呀。”
“噢,我的宝贝,咱们不是两个人吗?”
“不。”他说,“是三个人。”(https://www.daowen.com)
“您的朋友也来了?”说着,她便朝楼梯那边望去,露出一脸不知情的样子。
“不,我是说躲在大衣柜里那个朋友。”
“什么大衣柜?”她说,“您是不是神志不清了?您在哪儿看见一个大衣柜?我会把朋友藏在大衣柜里吗?我是把男人藏在衣柜里养汉子的那种女人吗?您一回家就疯了,把您的朋友和大衣柜都搅和到一起。我只认识您的朋友,那位名叫高乃依的呢绒商人,只知道咱们有一个放旧衣服的大衣柜。”
“噢!”金匠说,“我的好夫人,有一个坏小子给我通风报信,说你让咱们的律师当马骑了,而他这会儿就躲在你的大衣柜里。”
“是说我吗!”她说,“这些律师就会无理取闹,我根本忍受不了他们身上那股臭味,况且他们干什么活都不行……”
“得了!得了!我的心肝,”金匠接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人,也不想为了一个破柜子和你吵架。给我报信的那个人是一个做板箱的商人,我要把这个可恶的大衣柜卖给他,再也不想在咱们家里看见它。他用两个漂亮的小柜子来抵换,换来的小柜子就连小孩子也躲不进去,这样的话,那些嫉妒你德行的人,即便想恶意中伤或搬弄是非也找不到把柄了。”
“听您这么说,我就满意了。”她说,“我根本不在乎这个柜子,况且柜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咱们的衣服都送到洗衣房去了。明天早晨把这个不幸的柜子拉出去就是了。您想吃晚饭吗?”
“不想!”他说,“要是没有这个柜子,我会吃得更香。”
“我明白了,”她说,“把这个柜子从这儿搬走比改变您的主意还要容易……”
“好了!来人呀!”金匠对帮工和学徒们喊道,“都过来帮忙呀!”
转眼间,他手下的人就都来到跟前。他作为一家之主简短地吩咐下人把那个大衣柜搬走,于是,众人将这件用于偷情的家具搬出去,在经过大厅的时候,躲在柜子里的律师头朝下脚朝上待着呢,他不习惯这个姿势,在里面难免失去平衡,来回乱撞。
“走吧。”金匠老婆说,“走吧,没事!是大衣柜的框子在晃动。”
“不,我的心肝,是销钉活动了。”大衣柜也就不再挣扎了,乖乖地从楼梯上滑下去。
“喂,赶车的!”金匠招呼道。希贡赶紧把马车赶过来,一帮学徒把这个爱寻衅的大衣柜搬上马车。
“喂!喂!”律师在柜子里说道。
“师傅,柜子说话了。”一位学徒说。
“说哪国话呢?”说话间,金匠抬腿踹了这个学徒一脚,幸好这人的屁股不是玻璃做的。学徒一下子跌倒在台阶上,就再也顾不得去琢磨这柜子讲的是什么语言。在金匠的护送下,羊倌把这个大衣柜拉到河边,根本不听这件家具的高声辩解。在柜子上拴了几块大石头之后,金匠将大衣柜推到塞纳河里。
就在大衣柜像鸭子似的缓缓地扎到水里时,羊倌以嘲讽的口气喊道:“我的朋友,你游泳去吧!”接着,希贡沿着塞纳河岸边街道一直走到圣母院附近的圣朗德里码头街。他看到一处宅邸,辨别出这宅邸的大门,用足力气使劲敲门。
“开门!开门!国王有旨!”他说。
闻听此言,一位老人赶过来开门,此人正是放高利贷的维尔索里。
“怎么回事?”
“我受王室司法官派遣,特来通告,要你们今晚务必严加防范。”希贡回应道,“司法官已命令弓箭手严阵以待。因为搜刮过您钱财的那个罗锅又回来了。面对凶器您要顽强抵抗,因为他会毫不客气地送您上西天。”
说完这话,好心的羊倌撒腿就跑,一直跑到玛穆泽街,长枪队长科谢格吕常和帕斯格莱特在这条街的某所房子里吃晚饭,依照妓女们的说法,帕斯格莱特是当时放荡女人里最漂亮的,也是淫荡女子里最可爱的。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利剑般的眼光似乎能穿透一切。她看上去步履如此轻盈、快活,好像让整个天堂里的人都变得十分昂奋。她胆大妄为,俨然一个不知羞耻、丧尽天良的泼妇。在朝玛穆泽街区跑的路上,可怜的希贡感到很为难,担心找不到帕斯格莱特的房子,或者等他到那儿的时候,那两只野鸽子早已睡着了,但善良的天使暗中相助,让他一切如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他来到玛穆泽街时,临街的许多窗户都亮着灯光,好多头戴睡帽的脑袋从窗口探出来,其中有下等妓女、放荡的女人、女佣、丈夫、未出阁的小姐,这些人都是刚从床上爬起来,面面相觑,好像要点着火把,将一个小偷送上绞刑架似的。
“出什么事了?”羊倌向身边的一位居民打听,这人正手持一支长矛站在自己门口处。
“咳!什么事都没有。”这个老好人回答道,“我们还以为是阿玛尼亚克人杀到城里来了呢[3],原来是‘恶猴’正在暴打帕斯格莱特。”
“在哪儿打呢?”羊倌问道。
“就在那边,那所漂亮的房子,房子柱头上雕刻着长翅膀的蟾蜍。您听到仆人和贴身女仆的吵闹声吗?”
其实,那不过是人的喊声:“杀人啦!救命呀!喂!快来呀!”紧接着,房子里传来雨点似的暴打声,“恶猴”用粗大的嗓门说:“我打死你这个臭婊子!你倒是唱呀,骚货!啊!你还想要金币!这就是金币!”
帕斯格莱特呻吟着:“哎呦!哎呦!我要死了!救命呀!哎呦!……”这时传来铁器的打击声,传来这位漂亮女人的玉体重重地摔倒在地的声响,紧接着便是死一般的寂静。再往后,灯光也熄灭了,仆人、贴身女仆、客人以及其他人都陆陆续续回屋了,及时赶到的羊倌也随着他们走上楼梯。只见大厅里一片狼藉,瓶瓶罐罐都被打碎了,挂毯也被剪断了,桌布和餐具、饭菜散落一地,众人见此惊得目瞪口呆。
勇敢的羊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打开帕斯格莱特那间华丽卧室的门,只见她浑身不成样子,披头散发,酥胸袒露,倒在地毯上的血泊之中,此时,“恶猴”却愣在一旁,口中喃喃地嘀咕着,不知这出戏后面该怎么唱。
“喂!我的小帕斯格莱特,别装死了!好了,我给你拾掇拾掇!好啊!你这个奸诈的女人,不管是死是活,你倒在血泊里还是这么动人,我真想要你呀!”
说话间,狡猾的兵痞把她抱起来,扔到床上,但她全身僵直地倒下去,宛如缢死者的尸体。见此情景,这位妓女的情人以为得让自己的驼背挪个地方了,但这个狡猾的家伙在开溜之前却说:“可怜的帕斯格莱特!我怎么会弄死一个让我爱得如醉如痴的好女人呢!可我竟然把她杀死了,这事明摆着呢,她活着的时候,她那漂亮的乳房可不是这么软塌塌的!天主呀!她就像是一块金币躺在褡裢里。”
在他说话间,帕斯格莱特睁开眼睛,微微侧了一下头,看了一眼自己那结实、雪白的肌肤。她苏醒过来,对着长枪队长的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就这么说死人的坏话呀。”她微笑着说道。
“朋友,他为什么要杀您呢?”羊倌问道。
“为什么?明天法院要派人来这里查封,他既缺德又缺钱,跑过来埋怨我去伺候一位英俊的领主,这位领主愿意救我,让我免遭司法的惩罚。”
“帕斯格莱特,我拧断你的骨头!”
“算了!算了!”希贡说,直到这时,恶猴才认出他来,“就这点事呀?好了,我的朋友,我可给您带来一大笔钱!”
“从哪儿弄来的钱?”长枪队长惊奇地问道。
“到这边来,我悄悄告诉您。假如有三万金币夜里在梨树底下游荡,您就不弯腰去捡吗?可别让这笔钱糟蹋了。”
“希贡,你要是拿我耍着玩,我非杀了你不可,就像杀死一条狗那样;你要是真能把三万金币摆在我面前,我会使劲吻你,吻你哪儿都行,即使让我在河道边的阴暗角落里杀死三个平民,我也肯干。”
“您谁也不用杀。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她为那个住在西岱岛上的放高利贷者做佣人,这人就住在舅舅家附近。我刚得到可靠的消息,说这人今天早晨到乡下去了,走之前在他家花园里的梨树下埋了一坛子金币,他以为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偏巧那天早晨女佣人感到牙痛,到屋顶窗前透透气,不经意间把老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在了眼里,她跟我撒娇的时候把这事透露出来了。假如您发誓能分我一半,我会助您一臂之力,让您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墙头,然后您再顺着墙边的梨树爬下去。嘿!您还说我是个笨蛋、蠢货不?”
“不,当然不会!你是忠实的好表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假如你需要除掉哪个对手,我准会效劳,帮你杀了那家伙,即使那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再是你的表兄,而是你的亲哥哥。喂!我的心肝!”恶猴朝帕斯格莱特喊道,“把饭桌都摆好,把你的血迹擦干净了,你流的血算在我头上,我会给你补偿的,要用我的血来百倍补偿你。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受惊的小鸟压压惊。把你的裙子整理好,笑一笑,我想让你笑笑,去看看那个蔬菜炖肉,咱们接着做刚才没做完的晚祷。明天我要把你打扮得比王后还漂亮。这是我表弟,我要让他吃好喝好,为此,即使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扔出去也值得,明天我们会从地窖里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回来。使劲吃呀!吃火腿呀!”
转眼之间,在神甫说出“天主与你同在”这句话的工夫,整个鸽舍就破涕为笑了,就像刚才乐极生悲一样。只有在窑子里才会出现靠动刀子去做爱的场景,才会在狭窄的空间内掀起快活的风暴,这些都是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长枪队长科谢格吕格外兴奋,就像100个下课后疯闹的孩子,使劲灌他表弟喝酒,羊倌露出乡下人淳朴的本色,把灌他的酒全喝下去,并装出喝醉的样子,满嘴说胡话,一会儿说明天要把整个巴黎城都买下来,一会儿又说要借给国王十万块金币,可以在金子上拉屎撒尿,后来便一个劲地说胡话,长枪队长怕他说漏了嘴,以为他脑子里出现了幻觉,于是把他拉到外面,等到分钱的时候,真想剖开希贡的肚子,看看他胃里是不是有块海绵,因为他整整喝了一大桶叙雷讷佳酿。他们边走边聊,说了一大堆神学问题,而且越聊越糊涂,最终沉默下来,一直走到放高利贷者埋藏金币的花园围墙前。科谢格吕踩着希贡那宽宽的肩膀,爬上墙头,又跳到梨树上,身手敏捷,颇像是打家劫舍的好手,但维尔索里早就在此恭候多时,对着他的脖颈砍了一刀,接着又狠狠地砍了一刀,结果砍了不到三刀,科谢格吕的脑袋就搬了家,在脑袋落地之前还清楚地听见羊倌冲他喊着:“我的朋友,把你的脑袋捡起来吧!”
宽厚的希贡有一副好心肠、好品德,因此得到苍天的报答,他觉得这会儿也该返回议事司铎的家了,在天主的保佑下,议事司铎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变得格外简单了。于是,他大步流星地朝圣彼得牛头街走去,回到家后,他倒头便睡,睡得就像婴儿那么香甜,甚至不知道表兄弟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第二天,他还是依照羊倌的习惯,天一亮就起床了,然后来到舅舅的卧室,看看他是否吐痰,是否咳嗽,是否睡得香甜,但老女仆告诉他,议事司铎听到圣莫里斯的晨经钟声——圣莫里斯可是圣母院的第一个守护圣人,就毕恭毕敬地到圣母院去了,教务会的所有成员都要去巴黎主教府上用餐。闻听此言,希贡说:“议事司铎先生这么早出去会着凉、感冒、手脚冰冷的,他是不是昏了头呢?他是不是想早点断气呢?我给他把火烧得旺点,好让他回来暖和暖和。”
善良的羊倌走进议事司铎最喜欢待的那间大厅里,却看见老人就坐在椅子上,不由大吃一惊。
“嘿!嘿!比莱特这个疯婆子在胡说些什么呀?我知道您考虑周全,不会这么早就坐到神圣的祷告席上。”
议事司铎一句话也不说。羊倌像所有喜欢沉思的人一样,对任何事情都善于心领神会,当然知道老人时常会有一些怪念头,会和神秘的东西交谈,内心里想着许多事,嘴里喃喃自语,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出于敬意,况且也不想打断老人那玄妙的冥想,羊倌就离他很远坐下来,静等着他结束遐想,与此同时,他一声不吭地看着舅舅的脚趾甲,长长的脚趾甲好像要把鞋子捅破似的。接着,他又仔细地看了看舅舅的双脚,发现他小腿上的皮肉竟是深红色的,将裤腿都映红了,从裤子的布纹看过去,那双腿好像着火了似的,见此情景,他不禁大惊失色。
“他真是死了!”希贡内心里想着。
此时,大厅的门开了,只见议事司铎鼻尖冻得通红,做完祈祷回到家中。
“哎!哎!”希贡说,“舅舅,您是不是糊涂了?您得当心别在门口那儿待着,因为您刚才还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另一个和您一样的议事司铎呀!”
“啊!希贡,过去我倒真想有分身之术,但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要是这样的话,人可是太幸福了!你是不是看花了眼?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呀。”
此时,希贡转过头朝那把椅子望去,椅子上空无一人,您当然能想象出他有多么惊讶,他朝椅子走过去,在地砖上发现一小堆灰烬,灰烬当中冒出一股硫磺味。
“啊!”他惊诧地感叹道,“我承认,魔鬼对我确实很仗义,我要在天主面前为他祈祷。”
接着,他把此前的经过如实地讲给议事司铎听,讲魔鬼如何开心地秉承天意,帮助他光明正大地除掉那两个黑心肠的表兄,议事司铎极为赏识他的举动,而且对此非常理解,因为他的头脑还很清醒,很有理智,而且多次注意到魔鬼在暗中做了许多好事。因此,这位好心的神甫说,他本人常常碰到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随遇而安,淡看红尘,这可是严重的异端邪说,对此主教会议曾多次给予驳斥。
希贡家族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现在他们凭借祖上积累的财富,出资兴建圣米歇尔桥,在这座桥上,魔鬼被雕刻成天使的容貌,以此来纪念这段被载入史册的奇遇。
[1]这个绰号含“掠夺傻瓜”之意。
[2]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的精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养育者和教师;泽费罗斯,希腊神话中的西风之神。
[3]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拥护奥尔良公爵的阿玛尼亚克人为捍卫自身的利益与勃艮第公爵手下的武装力量发生激战,从而爆发内战,但内战结束后,依然有阿玛尼亚克武装分子在各地烧杀抢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