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人物妆饰有“溪蛮”色彩
1.人物热衷枫叶、蝶、蛾、鸟,并赋予其神圣性,与一般文献记载异趣
枫在古代文献中一般为悲伤忧愁的表征。如《山海经》:“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晋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30]如屈原《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31]如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32]唐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33]
但在此图中,显然并非如此。此图4号人物肩挑长棍之左头挑有衣帽,帽上有马兰花连续纹样及枫花枫叶连续纹样。6号人物巾前额正中戴有五彩蝴蝶饰,上插一束枫枝叶及五瓣枫花,胸前补子上有金色枫花枫叶满地纹样,肩背上及袖之手背前部、袖之手肘后部亦有此纹样,唯颜色不同。8号人物衣袍上覆盖颈后背及肩膀有一块T形补子,覆盖颈后背及肩膀,花纹均为枫叶,唯品种有所不同。颈后背为金色枫叶满地纹样,上有两只小黑鸟,一停一舞;肩膀为金色枫叶枫花满地纹样。9号人物半臂下着袍服,袍服仍可见前有补子,为红地枫叶枫花满地纹样。可见枫在此图中是同样具有驱邪的神性的。
蝶蛾,在古文献中的意义则丰富得多了。除了庄子梦蝶,梁祝化蝶等,还有作为迎春之物的功用。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桑蚕春茧动,花蝶夜蛾迎。”其自注:“大白蛾花,无贵贱悉戴之,亦以迎春物也。”[34]贾玺增《中国古代立春与元夕节象生头饰(中)——闹蛾》对此戴闹蛾民俗也有较为全面的总结。但此图中的蝶与蛾,除了有迎春之意,应别具意味。
据笔者的研究,此图戴蝶冠者为领队(班主),如此他所戴之蝴蝶冠便不止有闹蛾之意,应更有尊贵之意。理由有三:其一,他的工作相对轻松,他的举止最有权势。图中他侧身直立,左手背后,右手小指、无名指自然曲缩,其余三指自然伸出,似在吩咐某事;而6号人物俯身拱手,目光正与他相对,颇有领命阿谀献媚之状。其二,他佩带着戥子(如图3.6、3.7)。此亦已为麻国钧《〈大傩图〉综合论说》一文所指出。戥子又名戥称,是旧时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器,也是商人身价财富的象征。此人物所佩戥子盒为黑褐色,材质似为紫檀之类,自是值得佩戴。佩此戥子,除了避邪,主要还是为了收取演出银两等。其三,他袍服的补子图案为人物,无论织或染,最为费工,应是此团队经济能力最强者。

图3.6 《大傩图》戴蝶冠者所佩的戥子

图3.7 戥子 知不足小斋博客图片
另外,此图中蝴蝶装饰,如前列表,最为繁多。除了头上戴的,还可作为身上的衣饰。如7号人物胸背补子图案为绿地马兰花满地蝴蝶飞纹样,11号人物袍服胸前补子上有马兰花枝叶满地间有蝴蝶、蜻蜓飞舞图案,肩背有两排蝴蝶图案。

图3.8 苗族枫蝶图案(https://www.daowen.com)
对枫、蝶装饰如此之热衷,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现代苗族的枫木、蝴蝶妈妈崇拜(图3.8[35]),正如苗族创世古歌所唱,她们是苗族人民的始祖。[36]苗族主体现在虽然多偏处于贵州、云南,但远古黄帝时黄河中下游的“九黎”,尧舜禹时长江、淮河流域的“三苗”,春秋战国时期的荆蛮,秦汉南北朝时期的“五溪蛮”,均为现代苗族的先源。而唐宋时期,则是苗族分布变化较大的时期,“汉水中下游以东至淮河流域的多数苗族已逐步被融合而消失”。[37]而民族的融合,也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融合。此《大傩图》中枫、蝶等形象,应为民族文化融合之表现。
2. 戴蝶冠者胸前补子上的图案
笔者还注意到,戴蝶冠者胸前补子与肩膀上的人物图案,非常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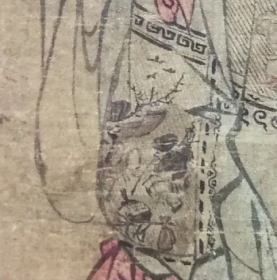
图3.9 《大傩图》戴蝶冠者胸前补子上的人物图案

图3.10 《大傩图》戴蝶冠者袍服肩膀上的人物图案
胸前补子图案(图3.9):图中有三人,左上人物纶巾执扇;右边人物头缠黑巾,舞傞步,似俯吹筒芦笙,至今犹为常见之苗人形象;左下人物为背面像,似才放下挑担。
肩膀上图案(图3.10):上有四人,左上人物只露左半身,似着道袍,左手斜挥扇子。右边人物为侧面像,正向挥扇者行揖礼,所着衣袍与此《大傩图》相似。两人下面是一背侧人物,也在向挥扇者行揖礼,似背背篓,背篓前有遮帘。与其平列稍下又有一人,正面像,似为仆从。
笔者初步判断,此人物胸前补子图案当为礼乐尊者图案,肩膀上为拜见尊者图案,此纶巾尊者为何人?笔者以为很可能就是在苗人中有神圣地位的诸葛亮。
综上,笔者以为此图人物妆饰有“溪蛮”色彩,即有现代苗、瑶等族先民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