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马若瑟的校订者
在1731年8月27日写给傅尔蒙的信中,马若瑟提到了自己最近收到的一本书。这本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书中的内容是关于神话学的,求证世界上所有最古老的民族都知道一个唯一真正的上帝,知道原罪以及拥有着对救世主的期盼。
从1733年开始,在此后的信札中,马若瑟再度提起过这位作者,我们能看出他已经成为了马若瑟的拯救者和最后的希望。
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1686—1743),更常见的名字是谢瓦利埃·拉姆赛,出生在苏格兰的额尔(Ayr)郡。由于他的父亲属于长老会,母亲属于圣公会,因此他很早就接触到了教义之争。在额尔郡的语法学校里,拉姆赛从Despauterus语法的摘要本中学习拉丁文。1702年至1704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文科,学习希腊语、数学、科学和哲学。此后,他似乎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学习过神学,但是却又不由自主地从惯有的神学争论中转入信仰一种虔诚而神秘的自然神论。
24岁那年,拉姆赛前往法国,在法国他拜会了伟大的坎布雷大主教费奈隆(Fénelon)。在费奈隆的影响下,拉姆赛信仰了天主教理论,并在此后五年里成为了他的朋友和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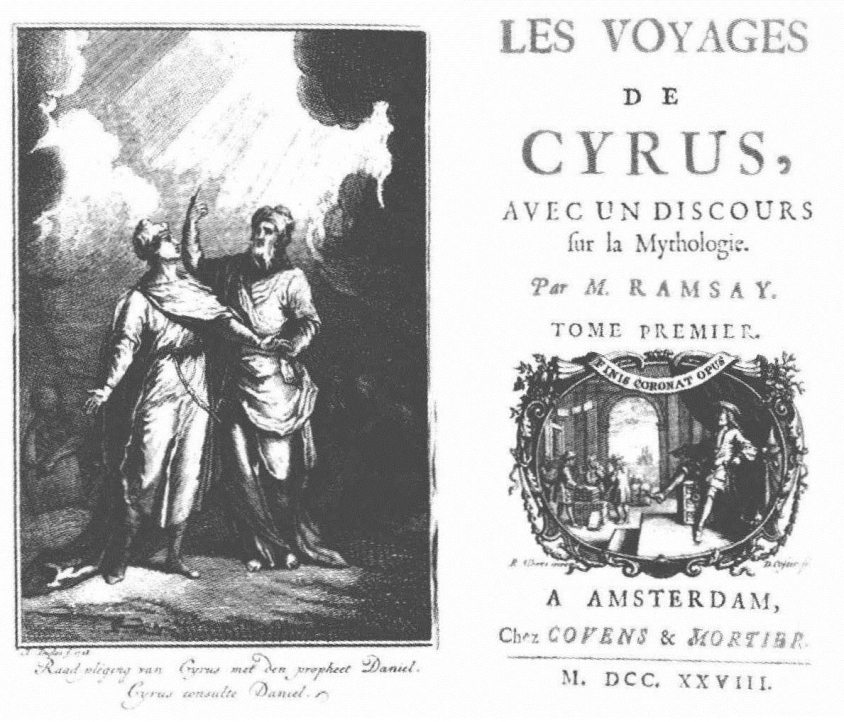
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的《居鲁士游记》(Les Voyages de Cyrus)扉页。
到了1718年,费奈隆大主教已于三年前逝世,拉姆赛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1723年他出版了费奈隆的一个简要传记。五年之后,1728年拉姆赛出版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作品《居鲁士游记》(Les Voyages de Cyrus),该书以法文、英文和德文多次重印[1]。
如今这部书已被淡忘,但请让我们再次重温它,如同当年马若瑟读到它一样。
年轻的居鲁士(Cyrus),在他建立波斯王朝之前,拜会过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圣人——如索罗亚斯德、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2]、梭伦(Solon)[3]、埃及的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4]以及其他很多人。最后,居鲁士在巴比伦的流放者中认识了但以理(Daniel)[5],并在以赛亚(Isaiah)[6]的预言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在书的最后部分,有一篇120页的关于古代神学和神话学的论文。文中论证了世界上的圣人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清楚表明了一些观点,那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史上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而人类的第一个祖先却背叛了上帝的恩宠,但人们仍有着对救世主的希望,因为他可以重建世界最初的和谐。
其中有3页是关于中国的神话的。那些让马若瑟欣喜的文段,在此略作缩写,如下所示:
在古老的《易经》注释本中,总是在谈到第一个和第二个“天国”。第一个天国被说成是当人类和上天结合在一起时,它就是一种完满的快乐状态……
在其他一些中国人称为“经”的典籍中,也提过第一个天国的愉悦——那里有着单纯的快乐、绝对的宁静,没有劳作之累,也没有苦痛和罪恶……
《庄子》一书也描述过这样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当人类在心灵上与天道融为一体,并实践公平之时……
《淮南子》里描述过第二个“天国”:“天堂的柱子被破坏了;大地支离破碎,回到最初的起点……大地反抗上天,宇宙的秩序变得有些混乱……”
但在同样古老的书籍中也谈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当有一个叫做“君子”的英雄出现之后,一切都将重现其最初的辉煌。无论是牧羊人,还是一国之君,他们都赋予“君子”一个同样的定义,即他是一位至圣者,万民之师和真理之所在。君子对于中国人,就如同波斯人的密特拉神(Mithra)[7],埃及人的奥西里斯(Osiris)[8],希腊人的墨丘利(Mercury)[9],印度人的婆罗贺摩(Brahma)[10]一样。
中国的书籍中也同样提到了“君子”的痛苦和矛盾,就好像叙利亚人所写的阿多尼斯[11]之死,而后阿多尼斯为了众人的快乐又再度复活……[12]
看起来所有的这些象征似乎都出自同样一个来源,即所有的民族有一个共通的传统,那就是在人间的上帝,他们称之为救世主,他用自身深重的苦难换取了罪恶的结束。但是,我不想就这一观点妄加评论,我的构想只是论述在所有的宗教中存在的,关于自然的提升与堕落,以及被神之英雄所重建的痕迹。
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马若瑟在给傅尔蒙的一封信中对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作出了反应:
当读到《居鲁士游记》这本书时,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了一段清晰的描述,关于在世界上最古老和著名的国度里,人类的三个发展阶段都十分明显地带有宗教的痕迹,包括中国在内。这在书的结尾部分的“论文”中有所提及。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就在中国书籍中所发现的那些优美的丰富的材料谈得太少了……
如果您和拉姆赛先生有私交,那么我相信您一定会把我以前寄给您的东西给他看,他也一定会非常乐意看到这些材料……
让我们回到这本书的内容上,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里,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为佐证,相互驳斥对方;特别是自亚当的堕落之后,基督就成为了所有人的希望。作者写到了作为间接上帝的完美象征阿多尼斯(Adonis),这是我们十分乐见的,也许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还希望作者能指出他在何处发现这些美妙的材料。我自己坚持这样一种写作态度,那就是在撰写任何关于古代中国书籍的文章时,一定要在栏外注解处标明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我查阅着这里的古老文献,而我自己一直这么做的目的和拉姆赛先生相同,为的是搜集世界上古老的传说。(1731年8月21日信)
在两个月后的长信中,马若瑟已从他所经受的小小的打击中(1731年11月10日信)恢复过来了,他在信中谈到了汉语的学习,他说:
我相信拉姆赛先生会很高兴学习足够的汉语来阅读我所写给您的东西,以了解那些都不是出自我的异想天开,我不是一个欺骗别人的骗子。
最后,在马若瑟1733年10月5日写给他(傅尔蒙)这个反复无常的朋友的告别信中——我们在那封信里得知马若瑟已经开始和拉姆赛直接通信了——傅尔蒙被告知在某些条件下要把以前马若瑟寄给他的论文转交给拉姆赛,因为马若瑟已经在傅尔蒙身上浪费了多年的时间——事实上,听起来好像是拉姆赛将向马若瑟要求得到这些材料。
如果您从著名的拉姆赛先生那里得知,我强烈地希望您把我的一些作品给他,您不应感到奇怪。原因就在于我知道他能用它们做些什么,也知道他一定会用它们做些什么。我太了解您了,可以想象得到您会拒绝我的这一愿望……
由于轻信和怀疑对宗教造成了伤害,而当我听说拉姆赛先生已经决定将他最为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为保卫我们的宗教而战之中,我感到多么高兴和安慰啊!他让我把对中国的研究资料寄给他,并向我保证它们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装饰上帝的殿堂。
我们没有看到过马若瑟与拉姆赛之间的通信,但是不难想象马若瑟给他写信的那种风格。他能做的只能是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工作:寄去一系列的信札,信中空白处注满了引文——汉语、注音、译文——谈论的是他能谈论的唯一话题,那就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古籍的帮助下使他们皈依天主教。
在拉姆赛的信札中,我们找到了马若瑟从自己写给傅尔蒙的最后一封信里摘录的只言片语,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拉姆赛把收到的资料都物尽其用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拉姆赛的全部时间都被撰写两部主要作品所占据。其中一部是论辩式的哲学神学论文,他称之为“巨著”——他为之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另一部草拟的题目是《七个对话》(Seven Dialogues)。
1743年,拉姆赛去世几个月后,他的一个年轻的苏格兰朋友罗伯特·弗里斯(Robert Foulis)看望了他的遗孀,把不少手稿带回了苏格兰,将这些手稿交给了一个爱丁堡的医生。他的名字是约翰·斯特文森(John Stevenson),是拉姆赛孩提时代的朋友。
这些手稿的名单——总共有32项——保存下来了[13]。第一部就是“巨著”——《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中的哲学原理》(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弗里斯于1748—1749年在格拉斯哥出版了该书。第二部就是《七个对话》,探讨的仍然是同样的哲学原理的问题。它应当作为一部伟大作品的介绍,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然而事实上却从没实现过出版计划。除此之外,还有三本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手稿——一本是《中国信件集录》共七卷(Recueil des lettres chinoises,7 in all),另一本是《傅圣泽神父和马若瑟神父的部分来信》,还有一本是《关于中国书籍和文字的论文草稿》。
我们并不清楚“中国信札”指的是什么,但从拉姆赛和他苏格兰朋友的通信中看得出来,他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和《七个对话》一同出版。
最后一项就是《关于中国书籍和信件的论述》(Dissertation sur les livres et les lettres de Chine),我们立刻辨认出那是马若瑟写有这个名称的论文题目,尽管词语“livres”和“lettres”的顺序被颠倒了。这篇论文就是本书中的“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一文。
然而现在已经无法找到拉姆赛这篇文章的任何存留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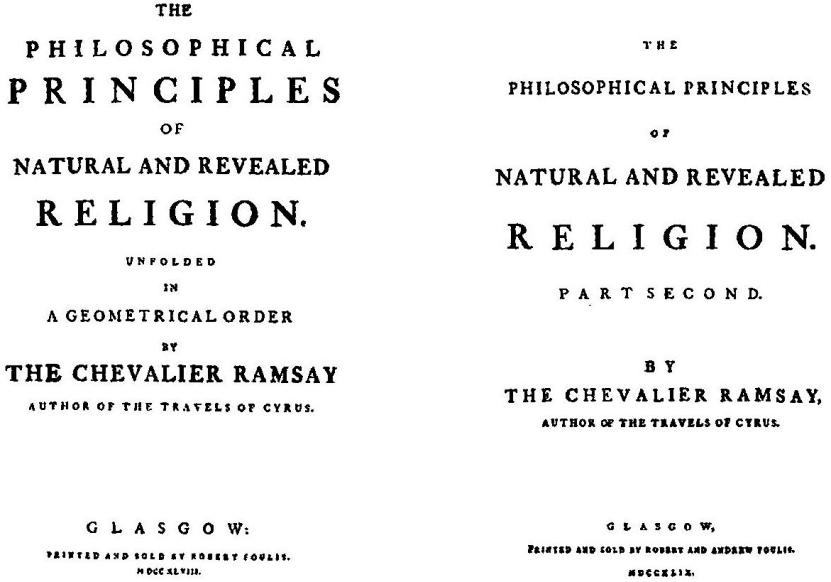
拉姆赛的《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中的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1748),第二部分包含有马若瑟的索隐学思想。
就“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而言,马若瑟极有可能也寄了一份抄本给拉姆赛,就像1725年他给傅尔蒙写第一封信时所做的一样,即把该文作为一篇简要介绍他如何用索隐学的方式阅读《易经》的文章。
七封中国信札的汇编摘录了马若瑟的来信,或者是在马若瑟书信的基础上有所改动,也许可以算作《七个对话》的一篇短小的附录。
大卫·古特贝尔森(David Cuthbertson)在《传记集》(Biographical Memoir)当中,发表了由他翻译的拉姆赛写的《费奈隆生平》(Life of Fénelon,1897),他说在拉姆赛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拉姆赛每天花数个小时学习汉语,以阅读相当数量的原文手稿。听起来这一点似乎成为了某种旁证,证实了在拉姆赛的家庭或朋友当中的这一传统。他们也许看到过他伏案工作,研究马若瑟的手稿和那些带有大量栏外中文注解的信札——我们已经在马若瑟1731年8月27日写给傅尔蒙的信中看到他对这一类的参考文献的执着[15]。(https://www.daowen.com)
拉姆赛有一封关于中国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这是写给前面提过的斯特文森医生的,日期是1742年4月24日,此时距马若瑟逝世已过了六年。信中,拉姆赛写道:
我很高兴你把《中国信札》寄给我们尊贵的朋友哈金森(Hutchinson)先生。他定要读过之后,才能对我的神话学体系作出正确的评价。在我想把《中国信札》添加上去之前,我就写好了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个对话。有了这些信札自然而然的参考,我可以想见这个对话会显得更加节略……
我完全同意你把《七个对话》分成两卷,第一卷包括六个对话,第二卷是最后一个对话和中国信札……
我计划把《七个对话》法文版最早的部分抄本寄给在罗马的教宗。他是一位非常睿智、善良、处事周密而思想开放的人[16]。我还准备了一份送给穆罕默德先生,土耳其驻法国的大使,他精通法语和欧洲学术。
我也决定给我在中国已故去的朋友的弟子们寄去十到十二份的抄本……[17]
前面提到的《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中的哲学原理》一书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在扉页上写着“是以几何学的规则来进行说明的”。这是一篇神学论证,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自然神论者、加尔文教徒和斯宾诺莎主义者进行驳斥,采用类似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s)的写作方式,即半数学式的风格,文中充斥着原理、定义、推论以及注释等内容。我们无须探讨这部分的文章。
第二部分包括了一篇有关在非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中存留的犹太一基督教教义遗迹的报告,大体上和《居鲁士游记》一书中关于古代神学和神话学的论文相似。不过,在这一部分,与《居鲁士游记》一书所截然不同的是,古老的中国典籍被放到了第一位,排在波斯人、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著作前面。
这篇文章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上帝的存在与标志”、“神圣的三位一体”、“中间上帝即弥赛亚的三个具体表现”、“人性的三个阶段”、“神性的三个阶段”、“世界通用的三个再统一的方法”。
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有这样的句子“让我们从中国人开始……”,紧跟着是“所有最古老的民族”或者是“那些源头可以追溯到接近大洪水时期的民族”。关于中国的内容共25页,有超过50段摘自中国古代作家的引文。其中三段取自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一书,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拉姆赛并没有指出其他的引文摘自何处,不过在序言部分他用通常的做法致谢:
我们谨向许多博学的欧洲人表示感谢,他们在中国生活多年,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研究这个古老民族所拥有的那些原始的、典范的著作,以及由官员和圣人们针对这些著作而作的评注,为我们提供了远在基督纪年之前的众多有关中国神话学的发现。
事实上,把拉姆赛的文章与马若瑟的《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18]相比,就会发现拉姆赛的引文都能从马若瑟的文中找到。有时候连几段引文出现的顺序都是一样的,而且它们的翻译都还算比较清楚。[19]
毫无疑问,拉姆赛手里拥有一份马若瑟最主要的索隐学著作的抄本或是该抄本的摘要本。[20]
拉姆赛提到,他尽自己所能从马若瑟的信札和手稿中了解和学习关于汉字的索隐学研究,但已明智地从中抽身而去。他也删去了《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中包含的那些详细说明单个卦象的部分。但就总体而言,马若瑟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索隐学式的阅读能从大量的引文中丰富地体现出来,其间还穿插着拉姆赛充满狂喜的慨叹,因为他们二人揭示了大洪水之前的种种神秘事物[21]。
拉姆赛没有在书中的任何一处提及马若瑟的名字,也许马若瑟自己要求拉姆赛不要这么做,这同此前摘录他在写给傅尔蒙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言相吻合。
至于说想从我的著作中沽名钓誉,我认为那意味着道德极为败坏。我已经来日无多,不过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请求上帝把我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了基督的荣耀和这些中国人灵魂的救赎,只愿他能找到别的人继承这一伟大的事业。
拉姆赛的《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中的哲学原理》一书,印刷精美,带着马若瑟希望传达给世人的信息,至今仍摆放在我们的案头,供那些有志于此研究的人阅读。
[1]原书本章注1:G.D.Henderson:Chevalier Ramsay,1952.
[2]毕达哥拉斯(?—?497 B.C.),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译者注
[3]梭伦(638?—?559 B.C.),雅典立法者。——译者注
[4]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埃及智慧之神Thoth的希腊名,相传曾著有魔术、宗教、占星术、炼金术等方面的书。——译者注
[5]但以理,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由于笃信上帝虽被扔入狮子坑而无损伤。——译者注
[6]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预言家。——译者注
[7]密特拉神,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2—3世纪在罗马帝国通称Mithras,成为广泛崇拜的对象。——译者注
[8]奥西里斯,古埃及的冥神和鬼判,易西斯女神(Isis)的兄弟和丈夫。——译者注
[9]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信使,司商业、手工技艺、智巧、辩才、旅行以及欺诈和盗窃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Hermes)。——译者注
[10]婆罗贺摩,梵天,梵,印度教主神之一,为创造之神,也指众生之本。——译者注
[11]阿多尼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Aphrodite)所爱恋的美少年。——译者注
[12]原书本章注2:拉姆赛说他从“一位非常睿智的绅士”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但“那位绅士却不愿透露其姓名,直到他关于相关内容的巨著出版”。这个人只可能是耶稣会士傅圣泽,中国索隐学者及Eleutheropolis地区的主教,拉姆赛曾在1724年前往罗马拜会他。(Witek,J.D.:Controversial ideas...Jean François Foucquet,1982,p.310)
[13]原书本章注3:Henderson,op.cit,p.243.
[14]原书本章注4:在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和Scotsman上面刊登的告示说明它们希望公开这篇论文的愿望已经落空了。
[15]原书本章注5:Henderson在其作品中曾引述说,“感到《中国信札》在风格上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很相似的推测是正确的,而在某些人名辞典里则非常天真地说,这种相似肯定不是拉姆赛学习汉语所带来的后果”。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来证明这一假定的正确性。拉姆赛肯定“学习过中国语言”,也就是说他仔细地审阅了马若瑟信札和手稿中注解部分的文本。
[16]原书本章注6:本尼迪克特十四世(Bebedict ⅩⅣ,1675—1758),又称教宗本笃十四,意大利籍教皇(1740—1758)。在1742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封信写就的时间——他颁布了通谕“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结束了中国礼仪之争。他被说成是一个“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以及无穷尽的快乐和机智的人”。(Encycolpoedia Britannica,11.Ed.,1911)
[17]原书本章注7:历史手稿委员会,《关于Laing手稿的报告》(Report on the Laing manuscrupts),爱丁堡大学,第2卷,第330—333页,1925年。
[18]此处采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二三五传“马若瑟”中的书名,第532页。——译者注
[19]原书本章注8:无论是拉姆赛,还是出版者,都把马若瑟法文注音中的很多人名和书名拼写错了。例如(蚩尤)Tchi-y-cou写成了Tchi-yeon,他是中国神话中第一个天国的叛逆者。但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当时,除了孔子,这些名字对读者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20]原书本章注9:就我们所知,当马若瑟把这篇论文寄给傅尔蒙时,他曾说过,这篇长达658页的文章,自己再没有额外的抄本了。但是他一定至少就某些章节做了誊写,因此才能把它们寄给拉姆赛。
[21]原书本章注10:在《居鲁士游记》一书中出现的中文引文和马若瑟摘自傅圣泽的引文,都没有出现在《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中的哲学原理》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