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月×日
功课在“马洛列特柯娃寓所”里进行,或者,换句话说:是在闭着幕、布置有道具的舞台上进行的。
我们继续表演对付疯子和壁炉生火这两个习作。
由于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的暗示,习作表演得很成功。我们是这样的兴奋和愉快,甚至于要求把这两个习作从头再演一次。
在等待中,我坐到墙跟前去休息一会。
在这里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很奇怪,没有什么显见的原因,放在我旁边的两张椅子突然倒下来了。谁都没有去碰它们,它们却倒下来了。我把倒下去的椅子扶了起来,又赶快扶住另外两张摇摇欲倒的椅子。这时墙上有一条狭长的裂缝投入了我的眼帘。这条裂缝愈裂愈大,最后,我眼看它变得有整堵墙那么高了。这时我才明白椅子是由于什么缘故倒下来的。原来,代表房间墙壁的幕布分开来了,在移动的时候,把东西随之拖走,所以把椅子拖倒了。谁在把幕拉开来了。
这就是舞台框的大黑洞,那儿有着托尔佐夫和拉赫曼诺夫的朦胧的身影。
随着幕的拉开,我心里发生了一种变化。
这变化可以用什么来比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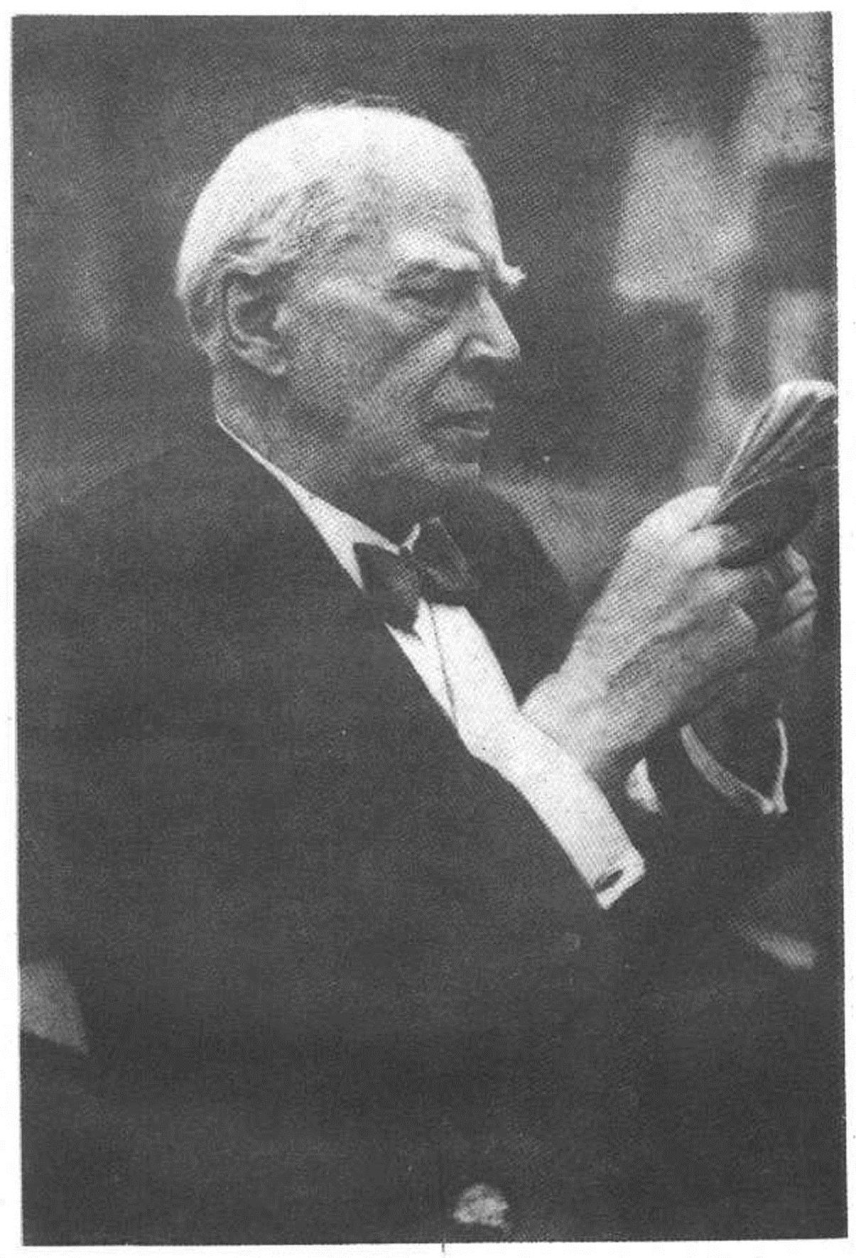
康·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摄于19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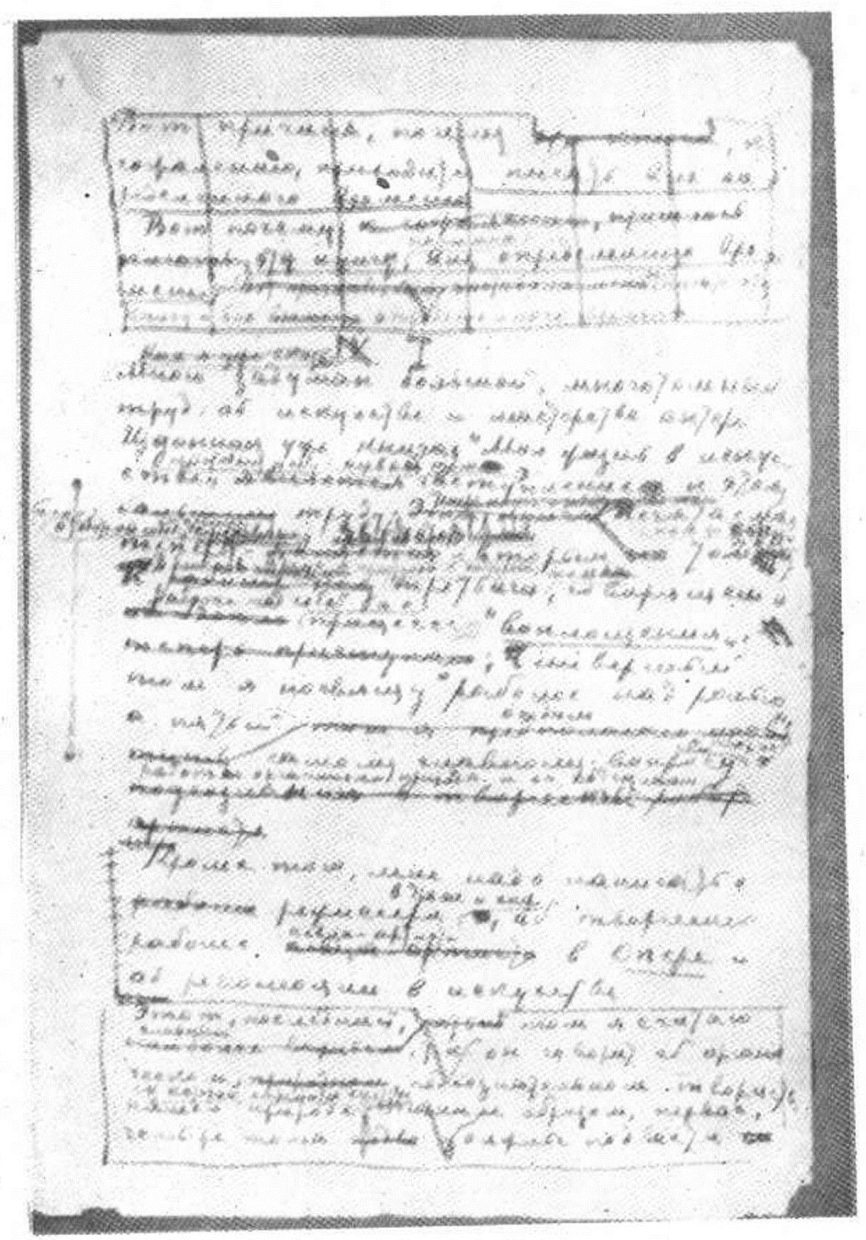
《演员自我修养》一书序言原稿的一页
请设想一下吧;我和妻子(假定我有妻子的话)同住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我们正在倾心谈话,脱着衣服,准备躺下睡觉,我们非常随便地在举止动作。突然间,我们看见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扇很大的门打开了,从那扇门里,有外人——我们的邻居在黑暗中望着我们。那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们并不知道。在黑暗中,总觉得人数很多。我们赶快穿上衣服,把头发梳理一下,举止尽可能审慎些,就象在作客似的。
这样,在我的心里,就仿佛弦乐器上所有的木栓突然都转动起来,把所有的弦都卷紧了似的,我刚刚还觉得是在自己家里,如今却仅仅穿着一件内衣处在人群中了。
真奇怪,这舞台框的大黑洞竟会破坏我们的悠闲自在之感。当我们在舒适的客厅里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无论你怎样站起来,无论你往哪里转身,——一切都很随便。第四面墙一打开,舞台框的大黑洞便成为主要的方面,你就得来适应它了。人们就是从这第四面墙向房间里观看的,所以你随时都得想到这第四面墙,考虑这第四面墙了。对于在舞台上交流的对手是不是方便,对于说话的人本身是不是方便,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那些不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而是坐在脚光那边的黑暗里的、我们所看不见的人能看到和听到。
刚才和我们一起在客厅里的托尔佐夫和拉赫曼诺夫,本来是平易可亲的,但现在一转移到黑暗里去,转移到舞台框外面去,在我们的心目中就变成了完全另一种人——严厉的、要求严格的人了。
我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在所有参加表演这个习作的我的同学们身上也都发生了。只有戈伏尔柯夫,无论在幕开着或在幕闭着的时候,都还是老样子。显然,我们的表演都是为了做样子,并没有什么成就。
“不,肯定地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学会不去注意舞台框的黑洞,我们就不能在表演工作中前进一步!”我暗下这样认定。
我和苏斯托夫讨论到这个题目。可是他认为,假使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习作,并且加上托尔佐夫的一些动人的解释,那一定会使我们转移对观众厅的注意的。
当我把苏斯托夫的建议讲给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听了之后,他说: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现在我就让你们表演一出动人的悲剧,我希望这悲剧能使你们不想到观众。
“事情就发生在这个‘马洛列特柯娃寓所’里。她嫁给那兹瓦诺夫,那兹瓦诺夫被某一个社会团体聘请做出纳员。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刚出世的孩子。母亲给那孩子去洗澡了。丈夫在翻阅票据,数钱,要注意,这是公家的票据和钱。因为时间晚了,他来不及把票据和现款交到他所服务的团体里去。一大堆陈旧的、染着油渍的钞票乱叠在桌子上。
“站在那兹瓦诺夫面前的是马洛列特柯娃的弟弟,是一个白痴,驼子,傻子。他看着那兹瓦诺夫怎样从一扎一扎钞票上扯下花纸头——封条——来,抛在火炉里,封条在火炉里明亮而轻快地燃烧着。白痴很喜欢这种喷起的火焰。
“所有的钱都数过了。一共有一万多。
“马洛列特柯娃乘着丈夫已经把工作做完的机会,招呼他去欣赏正在邻室浴盆里洗澡的小孩。那兹瓦诺夫去了,白痴学他的样子,也把纸头抛到火炉里去烧。因为没有封条了,他便把钞票抛进去。原来钞票比花纸头烧得更惹人喜欢。白痴陶醉于这个游戏中,索性把所有的钞票,公家的全部钱财,连同账单和票据都抛到火里去了。
“当那兹瓦诺夫回来的时候,正巧是最后一扎钞票喷起火焰的时候。他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不由自主地扑到驼子的身上去,用全力把他一推。驼子跌倒了,太阳穴撞在火炉的铁栏上。发狂的那兹瓦诺夫抢出已经烧着了的最后一扎钞票,绝望地叫着。妻子跑进来,看见弟弟直挺挺地躺在火炉旁边。她跑近前去,竭力要把他扶起来,但是扶不动。马洛列特柯娃发现弟弟的脸上有血,她叫丈夫,要他去拿点水来,但是那兹瓦诺夫一点也不理会她。他呆住了。于是她只好自己冲出去拿水,从饭厅里立时传来她的叫喊声。她生命的慰借——她心爱的婴儿在浴盆里淹死了。
“假使这悲剧不能使你们转移对观众厅的黑洞的注意,那么,你们的心肠简直就是铁石做的了。”
这一个新的习作以其闹剧性和突然性很使我们激动……但看来我们的心肠真象是铁石做的,我们竟不能把它演出来!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向我们提议,应该从“假使”和规定情境开始。于是我们开始互相谈些什么,但这并不是自由地发展想象,而是硬从自己心里去挤出什么,去想出某种虚构,这些,当然不能刺激我们去进行创作。
观众厅的磁力似乎比舞台上所发生的惨祸更来得有力量。
“既然这样,”托尔佐夫作了决定,“我们还是和观众厅隔开来,闭着幕来演这些‘惨祸’吧。”
幕闭了起来,我们的客厅又变得很舒适的了。托尔佐夫和拉赫曼诺夫从观众厅里回来,他们又变得很和蔼可亲了。我们开始表演。习作的前几段宁静的戏,我们演得颇为成功,但当事态演变到成为悲剧的时候,我的表演就不能使我满意了,我想表现出更多更多的东西,可是我的情感和气质都不够。我不知不觉离开了表演的正轨,走到自我表现的路子上去。
托尔佐夫的印象证实了我的感觉。他说:
“在习作的开头,你表演得很正确,到了末尾却是在做戏了。事实上你是从自己心里挤出情感来的,或者,照汉姆莱脱的说法,‘把热情撕得粉碎’。所以埋怨黑洞是多余的。不仅仅是它妨碍了你正确地在舞台上生活,就是闭了幕,结果也还是一样。”
“如果在开着幕的时候,妨碍我的是观众厅;那么,说实在话,在闭着幕的时候,妨碍我的是您和伊凡·普拉托诺维奇,”我承认。
“原来是这样!”托尔佐夫很好笑地喊起来。“伊凡·普拉托诺维奇!真是不妙啊!我们简直等于黑洞了!那么对不住,我们走吧!让他们单独去演。”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和伊凡·普拉托诺维奇用悲剧式的步子走了出去。其余的人也跟着走了。我们单独留下来,在没有旁观者,也就是在毫无妨碍的情形下试演起这个习作来。
真奇怪,在单独表演的情形下我们反而演得更糟。我的注意转移到对手身上去了。我竭力注意他的表演,批评他的表演,我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观众了。我的对手呢,他们也在注意地观察着我。我觉得自己既是看戏的观众,又是为了做样子而在演戏的演员。最后我们就愚蠢地,无聊地,而主要是毫无意思地相对表演着。
后来我偶然往镜子里望了一眼,心里很是欢喜,精神也提起来了,想起从前在家里研究奥瑟罗时的情景,当时也象今天一样,为了演给自己看,也曾望过镜子。我很乐于做“自己的观众”。自信心出现了,所以我同意苏斯托夫的提议,去邀请托尔佐夫和拉赫曼诺夫来,好把我们工作的结果表现给他们看。
但结果并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因为他们已经从门缝里偷看过我们单独的表演了。
据他们说,我们的表演比开着幕的时候所演的还要糟。那时候演得固然不好,但到底还谦虚而审慎,现在演得不好不用说,还加上了刚愎自用和放肆。
托尔佐夫总结了今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才明白:当幕开着的时候,有坐在脚光那边的黑暗中的观众妨碍我们;当幕闭着的时候,有坐在房间里的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和伊凡·普拉托诺维奇妨碍我们;当没有旁观者的时候,有对手妨碍我们,因为他变成我们的观众;而当我对自己表演的时候,作为自己观众的我,却妨碍作为演员的我。这样一来,无论你往哪里瞧,到处都有观众妨碍你。可是没有观众,演起来却又觉得无聊。
“比小孩还不如!”托尔佐夫责备我们。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沉默了一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只好暂时把这习作搁一下,先来研究注意的对象。注意的对象是这件事的祸首,下一次我们就从它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