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月×日
在今天的课上,我恍然大悟,把一切都弄明白了,我变成了“体系”的最热心的崇拜者。我看到,有意识的技术怎样引起下意识创作,使灵感自行流露出来,事情是这样的:
德蒙柯娃表演了“弃婴”习作,这场戏马洛列特柯娃曾经很出色地表演过。
要知道,德蒙柯娃所以这样热爱表演有孩子出场的戏,如《布朗德》中“襁褓”那场戏和这个新的习作,是因为她不久以前失去了自己唯一的爱子。这个消息是别人偷偷告诉我的,还没有证实,今天看了她所表演的习作之后,我就断定这消息是确实的。
表演时,眼泪象泉水般由德蒙柯娃眼里涌出来,她那做母亲的温存体贴使那块代表婴儿的劈柴在我们看的人心目中变成了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从当作婴孩包布的台布中可以感觉到这生命的存在。当剧情发展到婴儿死去的时候,德蒙柯娃的情感是这样的激动,以至于不得不停止这个习作,以免发生意外。
大家都深受感动。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满脸泪水,伊凡·普拉托诺维奇和我们也是一样。
当真正的生活本身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又何必去谈什么诱饵、线索、单位、任务和形体动作呢!
“这就是一个例子,告诉你们有机天性和下意识是怎么样创作的!”托尔佐夫兴高采烈地说。“它们完全按照我们艺术的规律来从事创作,因为这些规律不是捏造出来的,而是天性本身给我们的。
“但是,这样的灵感和想象并不是每一天都能得到。有时它们可能不来,那时候……”
“不,它们会来的!”德蒙柯娃偶然听到这段话,在极度兴奋中喊了起来。
她担心灵感一去不返,赶忙又去表演刚才演过的习作。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为了免得刺激这位年轻女人的神经,本想劝她不要再演,但很快地她自己就停了下来,因为她什么也演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托尔佐夫问她。“要知道,将来需要你不仅在第一次演出中,而且应该在以后各次演出中都演得很好。要不然,在首次演出中获得成功的剧本在以后几次演出中就会遭受失败,不再叫座了。”
“不!只要我有情感,就能表演。”德蒙柯娃替自己辩护。
“‘我有情感,就能表演!”托尔佐夫笑着说。“这不就等于说‘我学会浮水,就能游泳’吗?
“我明白,你想一开始就去接近角色的情感。当然,这是最好不过的。要是能一劳永逸地掌握到适当的技术,来重复那获得了成功的体验,该有多么好啊但是,情感是无法固定下来的。它有如流水,一来就去……所以我们不得不探索比较可靠的手法,来激发它,把它确定下来。
“手法可以任你们去选择!最容易做到的是形体动作,细小的真实,细小的瞬间信念。”
而我们这位易卜生主义者却厌恶地回避创作中一切形体方面的东西〔63〕。
凡是演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如单位、内部任务、想象虚构等等都尝试过了。但这一切手段都并不怎么吸引人,并不怎么可靠,同时也不容易做到。
尽管德蒙柯娃转来转去,回避形体动作,她最后还是回到这些动作上来,因为她不可能提出更好的手法。托尔佐夫立刻前来指引她。在指引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探寻新的形体动作,他尽力要她重复以前直觉地发现到而又出色地表演过的那些动作。
德蒙柯娃演得很好,她也有了真实感与信念。可是,这样的表演难道能跟第一次相比吗?!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对她这样说:
“你演得很好,可你表演的不是指定给你的那个习作。你已经把对象偷偷换掉了。我请你扮演的那场戏,手里应该抱着的是活的婴儿,而你给我们的印象却是用台布包着的一块劈柴。不错,你运用了同样的形体动作,你用灵巧的手去包那块劈柴。但是,照顾活的婴儿还需要许多动作细节,而你刚才把这些细节都删去了。譬如,在第一次表演中,当你给想象的婴儿打包被之先,你把他的小手小脚放好,当时你的确感到他的手脚在活动,非常喜爱地吻它们,嘴里轻轻地在叨念什么,脸上露出笑容,眼睛里却饱含泪水。这一切都很动人。可是现在这些细节都给删去了。那块劈柴当然也就没有小手小脚了。
“在第一次表演中,当你给想象的婴儿包着头部的时候,你生怕压着他的面颊,小心翼翼地抚摸它。你给婴儿打好包被后,长久地站在他的面前,眼里淌出母亲的喜悦和骄傲的泪水。
“让我们来纠正这些缺点。把这抱婴儿(不是抱劈柴)的习作再表演一下。”
德蒙柯娃在托尔佐夫的指导下,把那些细小的形体动作研究了很久,终于了解到,并且有意识地回想起第一次表演时自己下意识地所做的那一切……她感觉到手里抱着的是真的婴儿,于是泪水自然而然从眼睛中涌出。
“你们瞧,这就是心理技术和形体动作影响情感的一个例子!”德蒙柯娃表演完毕之后,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用赞赏的口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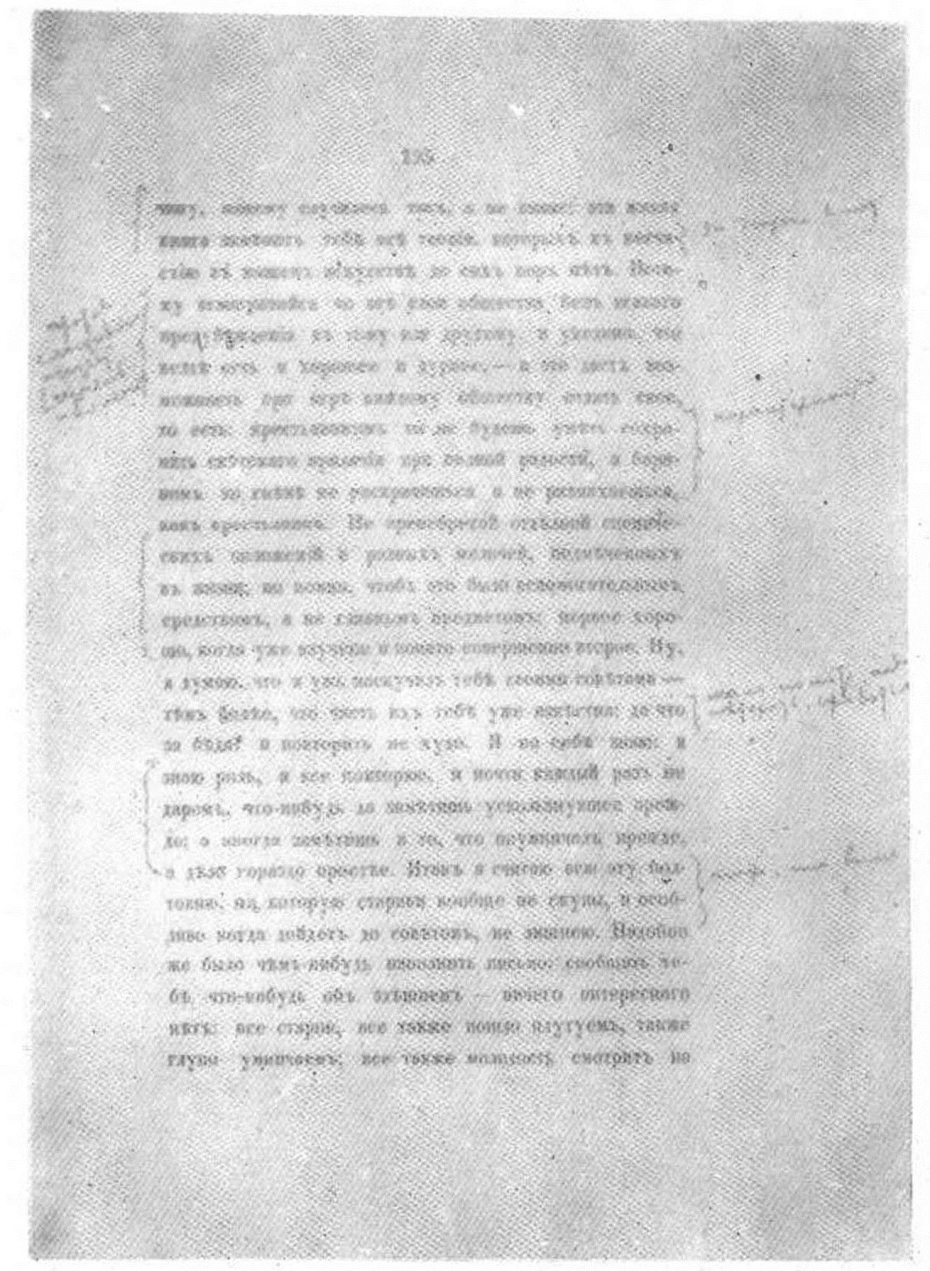
米·谢·史迁普金致谢·瓦·舒姆斯基信的一页。上有康·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作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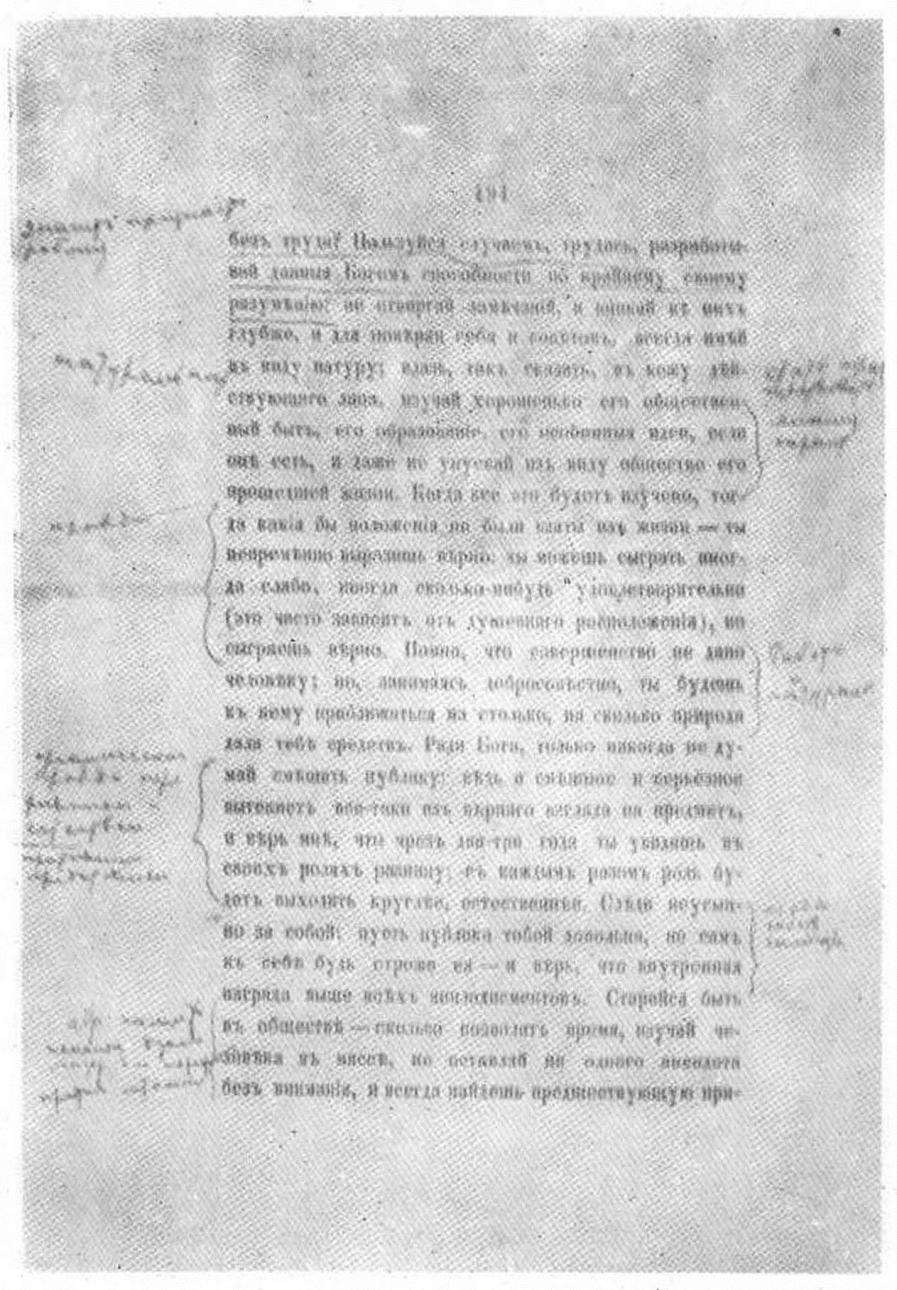
米·谢·史迁普金致谢·瓦·舒姆斯基信的一页。上有康·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作批注。
“这固然不错,”我有点失望地说,“不过德蒙柯娃这一次并没有那种强烈的体验,所以不论我和你都没有落泪。”
“没关系,”托尔佐夫说。“既然园地已经准备好,情感就能在这位女演员心里复活,强烈的体验就能到来,只要用一种动人的任务、有魔力的‘假使’或其他‘触媒’来诱导它就行。问题只在于我不想再去刺激德蒙柯娃的神经。可是……”他思索了一下,转过来对德蒙柯娃说:
“如果我给你加进这么一个有魔力的‘假使’,你将会怎样处理这块用台布包着的劈柴呢?假定你生了一个小孩,他挺逗人喜爱。你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但是……过了几个月,他突然去世。你悲痛得无以复加。可是命运可怜了你。你发现一个弃婴,也是小男孩,而且比以前那个更逗人喜爱。
“他正合你的心意!”
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刚刚讲完自己的虚构,德蒙柯娃立刻俯身在用台布包着的劈柴上放声大哭起来,于是……那种强烈的体验加倍有力地重现出来了。
我急忙跑到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跟前,给他说明此中秘密:他恰好触到德蒙柯娃实生活中的悲剧了。
托尔佐夫搔了一下头发,跑到脚灯前,想叫这可怜的母亲停下来,但他又很心爱她在舞台上所表演的,于是决定让她继续表演下去。
习作演完了,大家都平静下来,擦去眼泪。我走到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跟前,说出我的看法:
“德蒙柯娃刚才所体验的不是想象虚构,而是真情实事,也就是她本人生活中的悲哀,这一点难道您没有觉察到吗?所以,刚才在舞台上发生的情形,据我看来,应该算作是一种偶然的事故,一种吻合,而不是演员技术的胜利,不是创作,不是艺术。”
“那她第一次的表演是不是艺术呢?”托尔佐夫反过来问我。
“是的,”我承认。“那是艺术。”
“为什么呢?”
“因为是她自己下意识地记起她本人的悲哀,由于这种悲哀而激发起情感”
“这么说来,问题就在于我把保藏在她情绪记忆里的东西提示给她,而不是象上一次那样,由她自己,在她心里找到这种东西。但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演员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回忆在心里复活过来,也可以借助于旁人的提示而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记忆能保藏住所体验到的情感,并且在这种提示的推动下能使它活跃起来。这时候,你就不能不真诚地,也就是全身心地相信保藏在你自己记忆中的那种东西。”
“好,就算是这样。但是您应该承认,德蒙柯娃刚才所以能够恢复以前体验过的情感,并不是由于一些形体任务,也不是由于她对这些任务所具的真实感和信念,而是由于您提示给她的有魔力的‘假使’。”
“难道我反对这种说法吗?”阿尔卡其·尼古拉耶维奇打断了我的话。“关键几乎总是在想象虚构和有魔力的‘假使’上面。不过要善于及时引用这个‘触媒’。”
“究竟在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你可以走过去问一下德蒙柯娃,如果我过早地引用有魔力的‘假使’,当她在第二次表演中冷漠地把劈柴包入台布中的时候,当她还没有感觉到弃婴的小手和小脚,还没有去吻它们的时候,当她还没有把劈柴想象为活泼可爱的婴儿,小心翼翼地给他打包被的时候,她能够由于这种有魔力的‘假使’而激动起来吗?我深信在上述那种变化还没有发生以前,我把肮脏的劈柴比作美丽的婴儿,对她只能是一种侮辱。当然,由于我的虚构和她在实生活中经历过的悲哀有了偶然的吻合,她也可能放声大哭。这也可能激起她对死去的儿子真切的回忆。但这种哭泣是哀悼死者的哭泣,而在弃婴这场戏里,我们所期待的却是哀悼死者之中还掺和着对小生命的喜爱的一种哭泣。
“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当德蒙柯娃还没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把无生命的劈柴变成婴儿之先,她很可能厌恶地抛开劈柴,离它远远的,独自沉浸在那亲切的回忆中,涌出悲伤的眼泪。但这也只是哀悼死者的眼泪,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她第一次表演习作时所流出来的那种眼泪。当她重新看到并在自己的想象中感觉到婴儿的小手和小脚,当她的眼泪润湿了婴儿的身体之后,德蒙柯娃才象她第一次表演时那样哭起来了,这种哭泣才是习作所需要的,也就是掺和着对小生命的喜爱的一种哭泣。
“我把握住这个关键,及时投入一个火花,提示一个和她最深藏的回忆相吻合的有魔力的‘假使’,这就使她产生了真正的、强烈的体验,我认为这种体验完全可以使你们满意。”
“这一切是不是说,德蒙柯娃在表演中产生了错觉呢?”
“不!”托尔佐夫挥起手来。“这里面的秘密就在于,她所相信的并不是劈柴变成婴儿的事实,而是习作所表现的遭遇在生活中可能发生,这个遭遇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安慰。她相信自己在舞台上各种动作的真实性,相信动作的顺序、逻辑和真实;由于这些,她才感到‘我就是’,才激起有机天性及其下意识去从事创作。
“现在你们看到,通过形体动作的真实以及对形体动作和‘我就是’的信念来接近情感的这一手法,不仅在创造角色时可以适用,而且在刷新已经创造出来的角色时也可以适用。
“有了那些可以激起以前体验过的情感的手法,这真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没有这些手法,那一度降临在演员身上的灵感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一去不复返了。”
我感到很满意,下课后走到德蒙柯娃跟前,向她道谢,因为她清清楚楚地给我说明了艺术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以前对它是没有彻底弄明白的。
